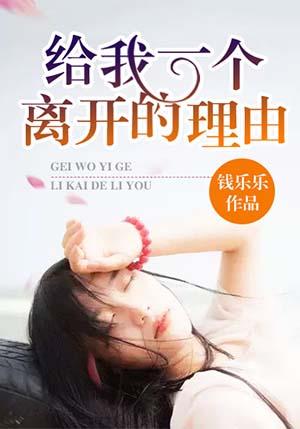630中文网>重生三国我郭嘉 > 第194章 演员就位死亡峡谷(第2页)
第194章 演员就位死亡峡谷(第2页)
再后头,黄巾余孽吊得更近了。陈四眼睛盯着那两辆空牛车,心里打鼓:不对,这车太轻。他正要让人分去一半到山腰去试探,前头“谷口棚”已经在风里晃动起来。
那棚不过是一架粗木,搭在道旁。棚下已经坐了几个人,穿粗布衣,手拿木碗,像刚从田里出来的农。旁边立了一块木牌,上书“借问水深浅”。牌很旧,像从别处搬来。正中有一只碗,碗里压着一枚铜钱。
清议四人一见这牌,立刻精神一振。为首那人翻扇,笑道:“妙,妙极。百姓借问水深浅,正好讲‘兴修与治安’。”他骑下马,端起那只碗,对着周围的“百姓”开讲。他讲得极好,句句不沾灰,字字落在“德”的线上。围观的人越聚越多,葛三喉一抬手,挑夫自觉把队形拉成弧,让出“讲台”。整个峡口,像一座临时的露天议事厅。
这就是郭嘉要的“外景”。他要让“清议”站在百姓中间讲“仁政”,让“黄巾”在旁边看到百姓愿意听,让“护运”从旁边慢慢通过。他要让人看见“礼”的效力,而不是“刀”的威能。等看够了,才给他们看“律”。
峡里风声一变。鸩已经进了谷。他与几名夜行人脱了斗篷,手里多了几根似乎用来挑担的竹竿。竹竿顶端包着麻。麻里,是油。他们在人群最外圈踱步,把竹竿挑在肩上,像挑着豆腐,轻轻撞一下,油香就像饭香一样散开。香不毒,不让人晕,只让人饿。
“饿,就会走。”鸩心里记下一句。他在人群里穿过,悄悄摸到了陈四身后。“看够了么?”他压低嗓子,“该走了,跟着‘诏运’走,把’清议’让在百姓里,别动。动了,他们反咬你‘惊驾’。”
陈四皱了皱眉,还是点了点头。他不知道跟着这个声音走,会走到哪儿。他只知道,这声音昨夜把他从火里拽出来,没有让他烧了自家炕。
——
峡谷最窄处,只有五骑并肩的宽。两侧岩壁在傍晚的光里泛着青。护运队在这儿把队形换成“一长蛇”:两辆空车在中,老吏夹中间,葛三喉在尾。清议的“讲台”在峡口,未入峡。黄巾的眼线被油香牵着,跟在队后。更远处,还有几双眼睛,或许属袁氏暗探,或许是“清议”的“清客”,他们戴着宽沿斗笠,目不斜视,却把一切读进眼底。
“现在。”郭嘉在城头看着砂盘,把一枚小铜钉轻轻往前推。砂盘上,峡道那条线的中段,钉影与另一枚钉影接上。接点写着两个字:谷门。
谷门不是关隘,是“位”。人站在位上,自己就会矜;矜了,就会慢;慢了,就会乱不了。
葛三喉在“位”上吹了一声短促的笛。挑夫们应声把两根麻绳往外一拽,只拽一寸。两侧岩隙里藏着的布幔缓缓垂下,像峡壁忽然生出两条更深的影。布幔不是为了挡人,是为了“把声音收住”。峡谷的回声被幔子吃掉一半,余下那一半像被低头的兽驯服。人群的噪渐小,脚步归齐。老吏从怀里摸出牙牌,朝随行的县吏亮了亮,县吏躬身,骑快马先行,去前面“借粮借药”。
“清议”的声音从谷口飘来,如同毫发无伤的雪,落在布幔的这一侧,就化了。陈四忽然意识到:自己赌不赢这种声音。他们的刀,斩不动“礼”。
谷中风忽暗了一层。阿芷骑着一匹小驽马,沿着谷底伊水的石滩缓缓前行。她没有靠近护运队,她只看石缝里的苔和水痕。她在找“失序”的迹象:马蹄印的交叠、呼吸的错乱、目光的漂移。她在判断“刀会不会要出鞘”。
“有人在石上撒了灰。”她忽道,“灰里有细砂,脚一踩会滑。”
“谁的?”随行小吏把声音压得很低。
“看脚印,像是伪装的‘清客’。”阿芷伸手从鞍旁的布囊里掏出一撮粉,掺在水里,泼到石上。粉遇水就粘,把灰砂暂时“封”住。“封一次,够一刻钟。”
她做完这件事,又抬眼看了看谷顶。谷顶有几只比鹞更静的鸟——不是鸟,是鸩的人放的“黑纸鸢”。它们不鸣,只换方位。阿芷知道,那是“上面的眼睛”。
她再往前,追上葛三喉。葛三喉看她,咧了一下嘴:“小娘子,这里风大。”
“风大,火就不好走。”阿芷淡淡回,“别让香油靠布幔。”
“晓得。”葛三喉把竹笛往腰间一插,冲她竖了竖拇指,眼角却在扫“清客”的动静。两名戴斗笠的“读书人”逐渐往队伍缝隙里挤。葛三喉把笛一抬,对上边影子做了个“压”的手势。幔上又落下一指宽的一缕暗影,像把他们的肩膀轻轻按回到“队形”里。
这章没有结束,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!
就在这时,峡口方向突然起了一阵不合时宜的喧哗。清议讲“仁政”的声线被一声突兀的哭喊切断。一个背着孩子的妇人跌坐在地,孩子脸色发青,胸口起伏急促,唇边有白沫。她哭:“他喝了河水,肚子疼。”
四个儒冠愣住。为首那人刚要说“召医”,阿芷已经下马,袖中银针如鱼游水,三指一扣,针落在孩子“水分”上。孩子抽了一下,白沫顿止,阿芷顺势按了“中脘”和“天枢”,又让人捧了一碗加了“石榴皮末”的温水。妇人手抖,阿芷扶着她喂。片刻,孩子的腹鸣渐平,脸色由青转白。
“是水里有藻。”阿芷起身,擦针,声音稳,“不是祟。”
围着“讲台”的百姓蜂拥过来,先向阿芷行礼,又去看那四位“清议”。儒冠为首的那位愣了片刻,忙接一句“修渠净水,便是仁政”。他的话没错,可这句话此刻落在百姓耳朵里,像一阵风吹过石。风不会止痛,针会。
“演员”彼此之间的“抢戏”,就这样发生了。阿芷不是要“抢”,她是要把“戏”从空处拉回实处。她轻轻对那位儒冠点头,算是“把台还给你”。她知道这些人得活着下去,明早还要上朝,和“律”打交道。她只是让他们知道,“仁政”的第一句不在纸上,在人的肚子里。
这时,谷顶的黑纸鸢忽然斜飞了一寸,随即在半空停住。鸩在崖阴里竖起耳朵,听到了远处金属轻碰的细响。他伸手,五指微张,像无声地抓了一把风。
“来了。”他对身边的人道,“在‘峡腰’。”
峡腰,是峡谷中段一个最微妙的转折处。路从石滩绕到靠河的岩边,水声在这儿大一度,人说话要靠近一点才听得见。若有人要“劫”,最容易在这儿动手——一声喊,队形乱,乱就出刀。
那两名“清客”在峡腰处忽然同时侧身,手里扇骨一抖,扇骨其实是薄匕。另有两处石背后,蒙面人翻出,手里是混着木屑与油的火袋。他们不打“护运”,他们打“名”。一袋丢向“诏运”车帘,一袋丢向“愿书”匣。
就在扇骨出匣的那一瞬,葛三喉的竹笛发出一声极短的“嘀”。两侧幔子上的灰色绒球同时落下,带动隐藏在缝里的“滑板”轻轻倾斜。薄薄的水从幔后流出,像忽然伸来的一只手,把两袋火“接”住,火袋落水,闷声熄灭。一名蒙面人脚在阿芷方才封过的“灰砂”上打滑,他还未来得及骂一句,长索从头顶落下,像一条柔软的蛇,绕住他的手腕,一扯,匕首入石缝。
夏侯惇的虎贲卫这才从幔后走出,兵刃未出鞘,先用木棍把人按翻,手肘一压,膝一顶,整套动作连半个喘气都不耽误。另一头,鸩的人把第三个蒙面从石背后“请”了出来,蒙面人的眼睛露在黑布外,里边既有惊,也有委屈——他没想到自己被“不沾血”的东西败掉:水、线、幔、灰。
“谁叫你们来的?”葛三喉把竹笛敲在石上,发出清脆的答问声。没人开口。阿芷走过去,轻轻按住其中一个人的手背,摸了摸他的虎口,再摸了摸他的颈侧:“不是匠人手,不是兵手,是写手。”她抬眼,“清客。”
儒冠为首的那人脸色白了白,随即涨红。他刚要说“我不知情”,葛三喉已把竹笛横在他前面的空地上,“老爷,您别动。今天讲了半日‘仁’,该讲‘律’了。”
请勿开启浏览器阅读模式,否则将导致章节内容缺失及无法阅读下一章。
相邻推荐:宿敌 黎明坠落 试情 人外系[gb] 豆柴咖啡 阡陌之环[刑侦] 知他风尘不可救 重生:继续爱我,可不可以 全球极寒:在房车当囤货女王 蝶笼 蝶笼 [蓝锁同人] 利己主义者也想成为热血漫主角 影后难撩 [崩铁] 星神直播,在线造谣 在饥荒末世当农场主后封神了 [崩铁同人] 翁法罗斯RPG 我的女友重生了 [哨向]入鞘 重生三国:吕布,一戟破万法 拥有洗脑能力的我却很少使用,用自己的手段将学校女生变成自己的性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