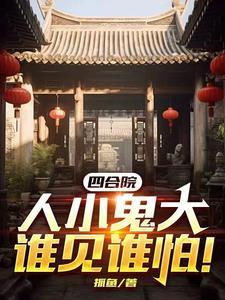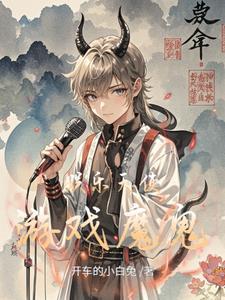630中文网>回到明朝当太后全文阅读 > 392和钟(第1页)
392和钟(第1页)
明年又是会试之年,临近年底,大批学子云集京师。
此刻,跟随皇帝到天坛祭天的宗室文武听着新编订的乐舞,看着新铸成的编钟,同样挺直了胸脯——经过将近十年的努力,在弋阳王奠壏的亲自督造下,终于成功铸成一套大型编钟,虽然不及曾侯乙编钟的逆天,但胜过以前太多。
——明朝自然有编钟,但一直以来君臣都不满意;当然他们不满意的不只是乐器,而是整个乐歌制度。
太祖建国初年,曾经制定了宴飨制度。当时殿中韶乐,其词出于教坊俳优,多乖雅道;十二月乐歌,按月律以奏;进膳、迎膳等曲,都用乐府、小令、杂剧,流俗喧哓,淫哇不逞。太祖很不满意。永乐十八年,北京郊庙成,太宗更定宴飨乐舞。奏曲肤浅,舞曲益下俚。
景泰元年,助教刘翔上书:“请敕儒臣推演道德教化之意,君臣相与之乐,作为诗章,协以律吕,以振励风教,备一代盛典。”
只是当时国家多事,景帝实在没精力在这上面花功夫。
建极改元,广求直言,礼乐制度就被提出来了。以前皇帝亲耕耤田,教坊司用杂剧伴奏,中间有狎语,大家也就一笑;但是现在太后当家,再不整肃,太后没脸,朝廷也颜面尽失。
因此,建极元年,礼部尚书薛瑄上奏:“御殿受朝,典礼至大,而殿中中和韶乐委之神乐观乐舞生,亵神明,伤大体。望敕廷臣议,岳渎等祭,当以缙绅从事;中和韶乐,择民间子弟肆习,年久则量授职事。”
詹事府詹事邹干也指出:“高皇帝命儒臣考定八音,修造乐器,参定乐章。其登歌之词,多自裁定。但历今百余年,不复校正,音律舛讹,应该厘正;且太常官恐不能当制造乐器、协调音律之任。”
汪舜华想到大宴时的伴奏,比后代的“擦掉一切陪你睡”高不到哪里去,以前没当回事,现在估计真就成了笑话。
于是行文各地,有臣工及山林有精晓音律者,礼送京师;这才有了后来的乐府。
建极二年,朝廷在百忙之中更定了乐章,严禁筋斗百戏之类掺杂期间,由翰林院会同各部门重新编订歌曲。虽然辞章带着陈旧的酸腐气,但好歹能摆上台面了,反正这种乐曲讲究的就是堂皇正大、不功不过。
只是汪舜华对着乐器很不满意——别的不说,就那编钟,不知道被曾侯乙编钟甩出多少条街:太宗皇帝铸造的也就16枚;曾侯乙编钟可是65枚!数量说明不了什么,关键是一钟双音!
汪舜华亲口问了,没这功能!
汪舜华当然知道曾侯乙墓在哪里,毕竟名声太大,纪录片就拍了好几部,国宝节目也经常说;但不可能派人去挖,要保护太难,技术上跟不上,何况天灾人祸的,说不定出土就变成浩劫。
甲骨文同理,虽然在安阳一带,这玩意估计还在被当成疗伤圣药被涂抹,但毕竟大半部分被埋着,万一身价飞涨,估计那地方很快会被挖的遍地狼藉,想想萌萌哒的妇好鴞尊、精美绝伦的云纹铜禁还有美轮美奂的莲鹤方壶,还是算了。实在不能因为自己的一点私心,让这些国宝遭遇任何不测,除非一切已经尘埃落定。
既然不能挖,就自己造,不相信明朝的技术比不上春秋战国的,虽然在青铜冶炼方面确实比不上。
于是和群臣商量:“大宴乃华夷宗室臣工所观瞻,宜举大乐。迩者音乐废缺,无以重朝廷。”
薛瑄马上跟上,从音乐的起源、发展、功用开始,认认真真的分析当前雅乐存在的问题,归结起来就是:观乎天文,以察时变;观乎人文,以化成天下。音乐不协,风气不正,您教化万方也就是一个美好的梦想!
话都说到了这个地步,内阁、礼部、太常寺也很支持。后代音乐只是娱乐,但在现在被赋予了政治含义:音乐不只是抒发感情、发泄情绪、表达情意而已,它的正与不正,关系着一国的治乱、社稷的安危以及个人的心境与健康,是严肃而绝对不能等闲视之的!听中音,纳和声,出嘉言,修正德,才是中正之道;否则黄钟毁弃、瓦釜雷鸣,就是礼崩乐坏、国将不国的节奏。
既然不满意,那么就做。
首先是选人。之前已经选了一批,不够,要制度化规范化,有优秀的音乐人才,允许官府推荐,也允许自己报名,由乐府定期考录。
其次是规范乐曲演奏。雅乐辞章已经调整,照着弄就行。
最后是乐器督造,其他的琴瑟箫笙笛篪搏拊柷敔什么的都还好,历代都有,关键是编钟,音色确实不够;太宗又仿宋景钟铸造了太和钟,高八尺一寸,拱以九龙,柱以龙虡,建楼于圜丘斋宫东北,浑厚是够了,但也太单调了。
因此,建极二年冬,和群臣商量重新铸造编钟。
但群臣普遍反对。
商辂就出班进谏:“铸大钟与铸大钱,都不利于积聚民财,反而会绝民资而鲜其继,造成民离财匮,世政不和。”
他提到了春秋时期周景王姬贵想造一套名叫“无射”的大型编钟,从臣子到伶官都不同意,就是因为耗费太大,国库承担不起;最后虽然勉强铸好,赶上周景王去世,就被说成是因为铸钟闹的。
汪舜华当然知道,编钟不是那么好铸造的,这东西流行于商周时期,随着青铜时代的落幕而逐渐退出历史舞台。首先用料是黄铜甚至黄金,造价很高,不是盛世根本就不要想。虽然周景王时期王室威望一落千丈,逼得他老人家常向诸侯打秋风,为此还留下了个“数典忘祖”的典故,但毕竟瘦死的骆驼比马大,能让府库空虚,可想而知真是烧钱。
而且技术要求很高,本来就是贵族圈子的游戏,随着战争和饥荒,工匠死去,技术失传,自然很难复制。汪舜华想要复制曾侯乙的传奇,群臣不知道这事,只是认为太宗已经铸造了编钟,如果没有大的突破,就不必另外再弄一套。
尤其接着就是改革,朝廷根本没有精力弄这事。
直到建极六年改革初步达到成果,至少官员不用跑地方督工可以留在北京研究、朝廷也有余钱,这件事才真正被提上议事日程。
太常寺卿夏衡,堪称书画大家,对音韵也有研究,但编钟制造也是头一遭;工部尚书白圭,一边忙着修北京外城,一边还得忙这事。两人会同精通音律的专家仔细商量,又把《考工记》等专业书籍翻出来,做成图纸,呈请太后审阅。
哪知汪舜华看了就说不行。她见过复制品,也看过专题片,曾侯乙编钟的奥秘就是它是合瓦式的,也就是两个小半圆合成,而不是正圆形或者椭圆形;另外就是加的微量金属比例,多了不行,少了也不行。
《周礼·考工记》有载:“金有六齐(剂),六分其金而锡居一,谓之钟鼎之齐。”也就是说编钟剂量铜6锡1,比例高了低了都不行。此外还需要精细的磨砺。接着翻书,《梦溪笔谈》有载“古乐钟皆扁,如合瓦,盖钟圆则声长,扁则声短,声短则节,声长则曲。节短处声皆相乱,不成音律。”扁钟发声短促,无延长音,圆钟有较长的延长音,在快速旋律中,各种频率的音会相互叠加而不成音律。
搞清楚了这个原理,实验仍然是漫长的工作。20世纪80年代初,湖北省动用国内最顶尖的专家、最尖端的设备,花费5年时间,耗资百万元才复制出3套,可想而知其中的艰难。
而现在,专家们以前的经验用处有限,先进的检测设备完全没有,一切只能靠摸索。
直到次年底,弋阳王二度进京,听说了这事,奏请过来观看。
老朱家的基因很强大,或者说宁王系家传渊源,弋阳王的哥哥宁王就是音乐奇才,他自己也精通乐律。弄清了原理后,又经过反复试验、反复磋磨,终于在建极九年秋天,做出了第一个符合要求的双音钟。
汪舜华知道双音钟研究成功,很是高兴,让他们带进宫来,亲自试了,非常满意;看了图纸,更是高兴,下令接着铸造,要做成一套音律齐全、气势宏伟的编钟。
万事开头难,头开好了,后面的事情就顺利多了。经过前后十八年的努力,终于在今年十月,做出了全套编钟。一共37件,按大小和音高为序编成7组悬挂在3层钟架上。最上层2组12件钮钟,中下两层5组共14件甬钟,外加1枚镈钟。钟架为铜木结构,横梁木质,绘饰以漆,横梁两端有雕饰龙纹的青铜套。中下层横梁各有佩剑铜人,以头、手托顶梁架,中部还有铜柱加固;编钟上同样用错金铭文标注音律。
编钟是乐器,更是礼器。按照周礼,天子的编钟乐悬是“宫悬”,也就是四面悬;诸侯的编钟是三面的“轩悬”。曾侯乙虽然使用了九鼎八簋,但在编钟使用上并没有僭越,老老实实的轩悬,只是把两面拉直做成曲尺形而已;皇帝是天子,理所应当的使用宫悬。
这时候的工部尚书已经是王复。他知道编钟的地位和意义,并不敢丝毫怠慢。汪舜华知道全套编钟铸成,很是高兴,让人搬进宫里。
汪舜华还在感叹刚铸成的编钟真的是光华夺目,皇帝的眼睛一下子亮了,如此庄重肃穆,精美壮观——这才是真正的皇家气度!这才是泱泱中华的风范!
没有成功复制出全套曾侯乙编钟,汪舜华的心里很是遗憾;但君臣不会这样想,因为这已经超出预计太多了,尤其全套双音钟,不仅极大地节省了人力物力,也代表着明朝冶炼水平达到新的高度。
听着编钟悠悠然然、清清灵灵的声音,皇帝身心顿爽,陡生一种无来无往,独步天地,溶入上苍的神异之感;尤其是编钟和编磬一起奏响,形成“金声玉振”的宏大效果,让君臣通体舒泰。
皇帝大喜过望,赐名“和钟”,并赐铭文:天高高,海滔滔,国泰民康,万年永保。弋阳王拿到了世袭罔替的资格,参与编钟铸造的官员工匠也受到了奖赏。
听着这恢弘庄重的曲调,文臣们默默颔首:这才是华夏正音嘛!
请勿开启浏览器阅读模式,否则将导致章节内容缺失及无法阅读下一章。
相邻推荐:搞友情不香吗 你又在乱来[电竞] 听说小师叔曾是师祖的情劫 渣过我的人都哭着跪着求原谅 穿成女主头号情敌后 清白之年 我在末世种田的日子 超能力者的一小时人生 重生成帝王掌中娇 原来是想谈恋爱 女朋友每天都要人哄 是时候退隐了[穿书] 我渣过的对象都偏执了[快穿] 我在古代做皇帝 穿成f4后我成了万人迷 山海有归处 没人知道我是神仙下凡 和我做朋友的女主都变了[快穿] 我被影后教做人 重生你不配[快穿]