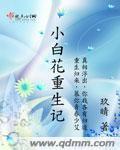630中文网>师生心灵对话单 > 第135章 课当睡眠成为奢侈品 一场关于安睡的生命对话(第1页)
第135章 课当睡眠成为奢侈品 一场关于安睡的生命对话(第1页)
凌晨两点的卧室里,蓝光在刘佳佳脸上投下惨淡的光斑。她盯着手机屏幕上的睡眠监测APP,数字像根扎眼的针——“深度睡眠17分钟”。这是她连续第三周在深夜刷到“凌晨三点的写字楼”话题,评论区里满是“我也没睡”的共鸣,看得她心口发闷。
隔壁房间的顾华正对着电脑揉太阳穴,白大褂扔在沙发上,领口沾着淡淡的消毒水味。作为急诊科护士,他刚上完通宵夜班,此刻身体累到发抖,大脑却像装了永动机,闭眼就是监护仪上跳动的绿色波形,耳边全是“嘀嘀”的警报声。
而对门的小云,突然在梦里翻了个身,嘟囔着“床前明月光,疑是地上霜……下一句是什么来着”。10岁的小姑娘踢掉被子,额头上渗着细密的汗,像是在梦里也在赶作业。
这三个场景,是当代人睡眠困境的缩影。中国睡眠研究会的数据像块冰冷的石头:我国能提供睡眠诊疗服务的机构超3000家,但睡眠疾病的诊断率和治疗率均不足1%。我们总以为“周末补觉”能弥补亏欠,可《自然》杂志的最新研究击碎了这个幻想:被剥夺睡眠后,与长期记忆相关的脑信号会不可逆减弱,补觉不过是自欺欺人,就像给干瘪的海绵浇点水,看似饱满了,其实根本回不到最初的状态。
耶鲁大学医学院教授迈尔·克利格在《睡个好觉》里,用40年临床经验敲醒我们:睡眠不是可有可无的“休息选项”,而是生命系统的“修复程序”。这位诊治过4万名患者的睡眠专家,见过太多因忽视睡眠而垮掉的案例:有连续熬夜的程序员在键盘前突发心梗,急救时血管里抽出的血像浓稠的糖浆;有长期失眠的教师患上焦虑症,讲台变成了让她窒息的牢笼;还有打鼾十年的司机,在高速公路上睡着,连人带车冲进了护栏……
今天,我们就以“师生对话”的方式,聊聊如何在24小时待机的时代,找回丢失的安睡。从阻塞性呼吸暂停到认知行为疗法,从道家“阴阳平衡”到现代心理学的“身心统一”,我们会发现:睡个好觉的本质,是学会与自己和解——就像潮水总要退回大海,你的身体也终会在某个时刻,渴望回归宁静的港湾。
一、教授的“深夜诊室”:课堂上的睡眠困境
教授推开教室门时,手里拎着个奇怪的袋子——里面装着睡眠监测仪、呼吸机面罩,还有几包不同品牌的褪黑素。他把东西往讲台上一放,金属器械碰撞的声音惊醒了趴在桌上补觉的顾华。
“先问大家一个问题——”教授的声音带着清晨的沙哑,像是刚喝完一杯热tea,“你们觉得‘不会睡觉’和‘不想睡觉’,哪个更可怕?”
顾华猛地坐直,椅子腿在地上划出刺耳的声音:“我选‘不会睡觉’。”他的眼下乌青比昨天更深,“就像我上完夜班,明明身体累到发抖,大脑却像装了永动机,闭眼就是患者的监护仪数据,这种无力感太折磨人了,感觉自己像个坏掉的机器,想停却停不下来。”
陈一涵推了推眼镜,镜片后的眼睛里布满红血丝:“我觉得是‘不想睡觉’。现在的短视频、游戏,总让人觉得‘再玩10分钟’,不知不觉就熬到凌晨,像是被什么东西牵着走。明明眼皮都粘在一起了,手指还在不停划屏幕,心里知道该睡了,可就是放不下手机,像有瘾。”
“两位说的都指向同一个核心——”教授在黑板上写下“睡眠主权”,粉笔灰簌簌落在讲台,“睡眠的‘主动性’正在丧失。克利格在书中说过一句话:‘爱迪生发明电灯后,人类就从‘日出而作’的自然节律,掉进了‘永远在线’的人造陷阱。’我们先从最危险的‘睡眠杀手’说起——那些藏在打鼾和失眠背后的疾病,它们可比熬夜更致命。”
二、看不见的睡眠掠夺者:当身体在深夜“缺氧”
“廖泽涛,你之前说你父亲总在夜里‘憋醒’,对吗?”教授突然看向后排那个总是打瞌睡的男生。
廖泽涛猛地惊醒,差点把桌上的保温杯碰倒:“啊?哦对!我妈说他打鼾像‘拉锯’,有时候突然没声音了,过十几秒猛地吸一口气,整个人都在抖,床板都跟着晃。”他的眉头皱成个疙瘩,“白天他总说头晕,血压也忽高忽低,上周体检报告出来,医生说他血管有点硬化。”
教授拿起讲台上的呼吸机面罩,透明的塑料罩在灯光下泛着冷光:“这很可能是‘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’。克利格的诊所里有个典型案例:一位45岁的货车司机,因连续发生追尾事故就诊,检查发现他每晚呼吸暂停达300次,每次憋气超过20秒。”
他突然按住自己的脖子,模仿窒息的样子:“就像潜水时被人按住口鼻,他的大脑在反复经历‘缺氧-惊醒-喘息’的循环,血氧饱和度最低时只有70%(正常人95%以上),白天能不犯困吗?最后一次事故,他连人带车撞进护栏,挡风玻璃碎成蛛网,他却一点都不记得发生了什么——缺氧让他短暂失忆了。”
这章没有结束,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!
刘佳佳下意识摸了摸自己的脖子:“可打鼾不是很常见吗?我爷爷打了一辈子鼾,身体照样硬朗。怎么判断是不是病?”
“看三个特征。”教授伸出三根手指,每根都像敲警钟,“第一,鼾声忽大忽小,不是平稳的‘呼呼’声,而是‘呼——(突然停住)——嗬!’这种锯齿状的节奏;第二,夜间频繁翻身,有时候会突然坐起来喘气;第三,白天不明原因嗜睡,开会、开车、甚至吃饭时都能睡着。”
他拿起人体模型,指着头颈部位:“从医学角度说,这种疾病是上呼吸道的‘夜间瘫痪’——清醒时肌肉能保持气道畅通,睡着后舌头后坠、咽喉松弛,空气就像被掐住的水管,只能艰难挤出。你们见过给气球放气吧?那种‘嘶——’的声音,就是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的典型鼾声。”
顾华突然想起科室的王主任:“我们主任就是这样!每天中午在休息室打鼾,声音能穿透两扇门,而且总在打鼾时突然惊醒,说自己做了噩梦。他总说‘老毛病了’,现在想想太危险了,他可是主刀医生啊!”
“更可怕的是它的连锁反应。”教授的语气沉了下来,“道家说‘气为血之帅’,呼吸受阻会导致血氧骤降,心脏被迫加班泵血,长期下来可能引发高血压、心梗甚至猝死。克利格遇到过最极端的案例:一位30岁的程序员,因呼吸暂停导致夜间血压飙到220130,却误以为是‘工作压力大’,直到某天早上醒来发现右手抬不起来,才知道自己中风了。”
廖泽涛的脸色发白:“那这种病能治吗?总不能一直任由它发展吧?”
“当然能。”教授拿起那个透明面罩,“轻度患者可以用‘口腔矫正器’,像戴假牙一样把下颌往前推,防止舌头后坠;重度患者需要佩戴呼吸机——就像给气道装个‘打气筒’,持续送气保持畅通,保证整晚氧气供应。但关键是要早发现,很多人觉得‘打鼾是睡得香’,其实是把身体推向深渊,等到出现高血压、心脏病再治,就晚了。”
三、认知行为疗法:给失眠者的“心理降压药”
“说完身体的病,我们聊聊‘心理的坎’。”教授放下呼吸机,转向刘佳佳,“佳佳,你说你躺床上就忍不住想‘今天没做完的事’,越想越清醒,对吗?”
刘佳佳的手指绞着衣角,声音小得像蚊子叫:“对!有时候明明很困,眼皮都打架了,一沾枕头就像‘大脑开机’,工作报表里的数字、孩子下个月的学费、父母的体检报告……全在脑子里转圈,像放电影一样。越逼自己‘别想了’,想得越厉害,有时候能睁着眼睛到天亮,看着窗帘从黑变灰,再透出光来,那种绝望感,真的不想再经历了。”
教授从袋子里拿出一本蓝色封面的日记:“这是克利格在书中记录的案例:有位中学教师因一次公开课失误,当晚失眠,满脑子都是学生的哄笑声。之后每次想到‘明天要上课’就睡不着,慢慢发展成‘只要躺到床上就焦虑’,哪怕周末没事也彻夜难眠,床变成了让她恐惧的地方。”
陈一涵推了推眼镜:“那该怎么办?吃安眠药吗?我听说有依赖性,越吃越离不开。”
“克利格最反对‘一失眠就吃安眠药’。”教授把日记本翻开,里面画着奇怪的图表,“他更推荐‘认知行为疗法(CBT-I)’,简单说就是‘重建大脑对“床”的信任’。比如‘睡眠限制法’——如果你每晚躺8小时却只睡5小时,就只允许自己在床上待5小时,哪怕躺着清醒也要起来看书,直到身体形成‘床=睡觉’的条件反射,而不是‘床=焦虑’。”
他举了个例子:“就像给偏食的孩子喂饭,你越追着喂他越不吃;反而告诉他‘不吃就收走’,他才会珍惜吃饭的机会。睡眠也是这样,你越强迫自己睡,越睡不着;反而限制在床上的时间,大脑才会对‘睡觉’这件事产生渴望。”
小景云突然举手,辫子上的蝴蝶结晃来晃去:“老师,我睡不着的时候数羊有用吗?我妈妈总让我数羊。”
教授笑了,眼角的皱纹像波浪:“有趣的是,克利格做过实验,数羊的效果不如‘想象平静的场景’。比如想象自己躺在草地上,阳光暖暖的,风吹过树叶沙沙响,花香一阵阵飘过来——大脑在处理这些画面时,会自然放松。这和道家‘虚静’的理念相通,都是让意识从‘紧绷’回到‘自然’,就像把卷起来的叶子泡在水里,慢慢舒展。”
他教了个简单的方法:“睡前试试‘478呼吸法’:用鼻子安静吸气4秒,屏住呼吸7秒,然后用嘴缓慢呼气8秒,想象焦虑随着气息排出体外。刘佳佳可以试试,上周有个失眠的学生告诉我,她用这个方法,三周后入睡时间从1小时缩短到20分钟。”
刘佳佳默默记在手机备忘录里,屏幕亮起时,她看到自己昨晚的睡眠曲线,像条挣扎的心电图。“我以前总觉得失眠是意志力不够,现在才知道,原来可以用科学的方法调理。”
请勿开启浏览器阅读模式,否则将导致章节内容缺失及无法阅读下一章。
相邻推荐:龙门秘录 金手指是看广告 亡国公主靠考古直播续命 龙皇崛起:我,蛟龙奥鲁古 女主角过于帅气 ABO百合futa水仙 女帝洛璃的烦恼 苏塘镇的情爱回忆1998 前夫哥你病得不轻啊! 我是坏女人!你们干嘛争着宠? 十二门徒书:黑胶皇后阿狸 科举:寒门毒士 雨涌风起 后宫御宴 将皇宫里的母猪统统肏服在我的胯下 我高考落榜去当兵 真武辰尊 伏羲异世录 天幕直播:带着老祖宗们玩遍诸天 穿越成寡妇,我的媳妇竟然是男的 美女同桌总掐我,从抵抗到真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