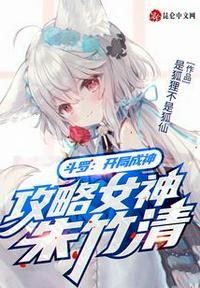630中文网>冰阳之歌 > 第362章 锁定远方去采访诺贝尔文学奖故乡(第1页)
第362章 锁定远方去采访诺贝尔文学奖故乡(第1页)
诺奖的标准,谁懂?
——题记
汽车的轮胎碾过北欧清晨的薄雾,车窗外的针叶林像被冻住的绿色浪潮,一直漫到天际线尽头。导航屏上“斯德哥尔摩”的字样逐渐清晰时,我攥着笔记本的手忽然松了些——指节因为一路用力而泛着淡淡的白,此刻终于能舒展地贴在粗糙的纸页上,感受那些提前写下的采访提纲在指尖下微微凸起。这场从中国南方小镇出发,跨越七个时区的采访,终于要落在诺贝尔文学奖的故乡土地上。
出发前的那个深夜,我在书桌前整理行李,台灯的光晕里摊着近十年的诺奖获奖名单。从2012年的莫言到2022年的安妮·埃尔诺,从石黑一雄笔下的移民故事到奥尔加·托卡尔丘克书中的魔幻现实,每一个名字旁边都密密麻麻记者读者的提问,有的是打印出来的邮件截图,有的是手写的便签:“他们写的故事离我们那么远,为什么能得诺奖?”“诺奖的标准到底是什么?是文笔好,还是故事深刻?”“我们身边那些写小说的作者,永远没机会靠近这样的奖项吗?”这些问题像细小的灯,一路照亮我辗转机场、车站的漂泊路——在广州白云机场等转机时,我对着登机口的玻璃幕墙反复默念;在法兰克福机场换乘火车时,我把笔记本摊在膝盖上,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田野发呆;甚至在斯德哥尔摩机场取行李时,还下意识摸了摸口袋里的名单,生怕这些疑问被落在陌生的异国他乡。
那时我还没意识到,“采访诺奖故乡”早已不是一个简单的任务。它更像一场寻找答案的旅程,一端连着遥远的斯德哥尔摩,另一端连着中国无数个基层作者的书桌——那些在邮局里写小镇故事的人,在医院里记病房日常的人,在田埂上写庄稼生长的人,他们或许从未想过自己的文字能和诺奖产生关联,但他们的困惑、他们的坚持,恰恰是我此行最该带回的答案。
抵达斯德哥尔摩的第一站,不是庄严的皇家科学院,也不是游人如织的诺贝尔博物馆,而是老城区一条窄巷里的二手书店。巷子很静,只有偶尔驶过的自行车铃响,阳光穿过巷子上方交错的电线,在石板路上投下细碎的影子。书店的木门上挂着一块褪色的木牌,用瑞典语和英语写着“时光之书”,推开门时,门轴发出“吱呀”一声轻响,像是在跟过往的岁月打招呼。
店里的空气里混着旧书的油墨香和木质书架的味道,暖黄色的灯光从天花板上垂下来,把每一本书都照得温柔。木质书架几乎顶到天花板,上面摆着许多诺奖得主的初版作品,有的书脊已经磨损,露出里面的牛皮纸,有的书页间夹着泛黄的便签,有的是读者的批注,有的是书店老板手写的推荐语。老板是位头发花白的老人,戴着圆框眼镜,正坐在收银台后翻一本厚厚的诗集,听见动静抬头看我,眼里立刻露出笑意。
听说我来自中国,老人放下书,从收银台后走出来,脚步有些慢,却很稳。他绕到书架的最里面,踮起脚从顶层抽出一本莫言的《红高粱家族》,书的封面已经有些卷边,却被保存得很干净。他翻开扉页,指着上面贴着的一张褪色照片说:“这是2012年莫言获奖时,我们书店举办读者交流会的场景。”照片里的人挤在小小的书店里,有人举着酒杯,有人捧着书,脸上的笑意和此刻老人脸上的一模一样。“那天来了很多人,有读过莫言作品的,也有没读过的,大家都想知道,什么样的中国故事能让全世界看见。”老人的英语不太流利,每说一句话都要顿一顿,却格外认真,“后来我们进了很多本《红高粱家族》,慢慢的,有人在书里夹便签,说读的时候好像能闻到山东的泥土味,能看见风吹过高粱地的样子——你看,这就是文学的魔力,它能把那么远的地方,拉到你眼前。”
我接过那本书,指尖拂过照片里人们的笑脸,忽然想起出发前见过的基层作者老周。老周在南方小镇的邮局工作,今年五十八岁,头发已经白了大半,却还保持着手写稿子的习惯。他的书桌就在邮局的休息室里,靠窗的位置,上面摆着一摞摞稿纸,有的写满了字,有的只写了开头,旁边还放着一个旧茶杯,杯壁上印着“先进工作者”的字样。
老周写了三十年短篇,笔下全是小镇居民的生活:张婶的裁缝铺里,缝纫机“哒哒”响着,缝补着小镇人的日子;李叔的修车摊前,总是围着一群孩子,听他讲年轻时跑运输的故事;夏天的傍晚,孩子们在河边捡贝壳,把笑声丢在水里,跟着波浪漂很远。去年他的文集《小镇记事》出版,印数只有一千册,还是出版社的朋友帮忙争取的。书出来那天,老周抱着书去镇上的各个角落送,给张婶送一本,给李叔送一本,给河边捡贝壳的孩子们每人送一本。
后来我去小镇采访他,他从抽屉里拿出一本《小镇记事》给我,书里夹着好多张老照片,有的是张婶裁缝铺的样子,有的是孩子们在河边的合影。“我写的都是身边的事,没想过能出版,”老周摸着书的封面,眼里闪着光,“但每次有人跟我说‘这写的就是我家的事’,我就觉得值了。有次张婶拿着书来邮局,跟我说‘你把我年轻时做衣服的样子写下来了,我家闺女都没见过呢’,那天我高兴了好几天。”
这章没有结束,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!
那时我还没把老周的写作和诺奖得主的创作联系起来,可在斯德哥尔摩的二手书店里,听着老人的话,摸着《红高粱家族》里的照片,忽然明白——老周笔下的小镇和莫言笔下的高粱地,其实藏着同一种力量。这种力量不是华丽的辞藻,不是宏大的叙事,而是用具体的人和事,连接起不同人的生命体验。就像老周的文字能让张婶想起年轻时的自己,莫言的文字能让瑞典的读者闻到山东的泥土味,这种“连接”,或许就是文学最本质的意义。
离开二手书店时,老人把那本《红高粱家族》送给了我,还在扉页上写了一句话:“好的文字,是跨越山海的桥。”我抱着书走在窄巷里,阳光刚好照在书的封面上,“红高粱”三个字像是活了过来,在我眼前晃出一片火红的高粱地,也晃出南方小镇的河边,孩子们捡贝壳的笑脸。
第二天,我去了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地——瑞典学院。学院坐落在斯德哥尔摩老城区的中心,是一座白色的建筑,门口有两座石狮子,看起来庄重又安静。负责接待的工作人员是位中年女士,名叫卡琳,她穿着一身深色西装,说话温和却很有力量。她带我走进学院的会议室,推开门的瞬间,我忽然屏住了呼吸——会议室很大,中间摆着一张长长的木质长桌,周围放着十几把椅子,阳光透过彩色玻璃窗,在桌子上投下斑斓的光斑,像撒了一把彩色的宝石。桌子上摆着历年的诺奖获奖证书,每一份证书的设计都不一样,有的印着获奖者的手稿,有的画着他们笔下的场景,有的则是简单的线条,却透着满满的诚意。
卡琳指着那些证书说:“每年九月到次年十月,评委们都会在这里讨论获奖人选。很多人以为我们会争论‘这部作品够不够深刻’‘文笔够不够华丽’,其实不是的。我们讨论最多的,是‘它能不能让更多人听见那些被忽略的声音’。”她拿起一份安妮·埃尔诺的获奖证书,证书上画着一个女人在厨房做饭的场景,很普通,却很温暖。“安妮·埃尔诺写自己的母亲,写工人阶级的生活,那些琐碎的、真实的细节,比如母亲在厨房里擦桌子的样子,比如一家人吃饭时的对话,很多人看了之后说‘这写的就是我的母亲’‘这就是我的生活’。”卡琳的眼神很亮,“诺奖从来不是给‘最好’的作家,因为‘最好’没有标准。它是给那些能让不同地方、不同身份的人,在文字里找到共鸣的作家——这就是我们的标准。”
我坐在会议室的椅子上,看着桌子上的证书,听着卡琳的话,忽然想起旅途中遇到的另一位基层作者小林。小林是位90后护士,在南方一座城市的儿科医院工作,轮班的间隙,她总喜欢把手机拿出来,在备忘录里写病房里的故事。她写患白血病的小女孩朵朵,每天早上都会偷偷给玩偶打针,说“要让玩偶先好起来,这样我也能快点好”;她写陪孩子治病的奶奶,每天晚上都会在走廊里偷偷抹眼泪,却从不在孩子面前哭;她写医生和护士熬夜抢救病人后,坐在护士站里吃凉掉的盒饭,互相打气说“明天会更好”。
小林的文章没有发在大的平台上,只发在医院的公众号上,每篇文章的阅读量也不算高,最多的时候也就几千。但每次发完文章,都会有很多人在评论区留言:“看哭了,我家孩子也在儿科住院,谢谢你们的照顾”“护士姐姐辛苦了,你们也是孩子的英雄”“朵朵要加油,一定会好起来的”。有一次,小林跟我说:“有个家长因为孩子的病情很焦虑,看了我写的朵朵的故事后,跟我说‘原来还有这么多孩子在努力,我们也不能放弃’。那一刻我觉得,我写的这些东西,比任何奖项都重要。”
原来无论是诺奖得主笔下的宏大叙事,还是基层作者写的微小日常,核心都是“看见”——看见那些被忽略的角落,看见那些平凡人的光芒。安妮·埃尔诺看见母亲的一生,小林看见病房里的坚持,老周看见小镇的温暖,他们都在用文字把这些“看见”记录下来,然后传递给更多人。而这种“看见”和“传递”,不就是文学最珍贵的价值吗?
采访的最后一天,我去了斯德哥尔摩的海滨公园。公园里很安静,只有海风拂过树叶的声音,还有偶尔传来的鸟鸣。远处的海面波光粼粼,像撒了一把碎银,几只海鸥在海面上飞翔,飞得很高,很远。公园里有一座诺贝尔的雕像,雕像前的石板路上,刻着不同语言的“和平”“希望”“梦想”,阳光照在上面,每一个字都闪着光。
我坐在雕像旁边的长椅上,拿出笔记本,把这些天的采访记录一一整理。从二手书店老人的话,到卡琳的解释,再到老周和小林的故事,那些片段像拼图一样,慢慢拼出了“诺奖标准”的样子。我忽然明白,自己寻找的“诺奖标准”,其实从来不在复杂的评选规则里,而在每一个作者与读者的连接中——就像莫言笔下的红高粱,连接了中国山东与瑞典的书店;就像老周写的小镇故事,连接了邮局职员与小镇居民;就像小林写的病房日常,连接了护士与患者。
这章没有结束,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!
海风拂过脸颊时,我在笔记本上写下:“诺奖的故乡不是一座城市,不是斯德哥尔摩的某条街道,而是每一个作者用心记录生活的地方;诺奖的标准不是一套冰冷的规则,不是评委们的争论,而是‘真正看见他人,并让他人被看见’。”
返程的飞机上,我把那本《红高粱家族》放在膝盖上,偶尔翻开看看。飞机穿过云层时,我看着窗外的云海,想起老周书桌前的稿纸,想起小林手机里的备忘录,想起那些基层作者的脸——他们或许从未想过自己的文字能走到远方,却始终在自己的角落里,认真地写着身边的故事。而对于我们这些文学路上的同行者来说,真正的价值从来不是追逐远方的奖项,不是羡慕诺奖得主的光环,而是扎根基层,倾听那些平凡的声音,记录那些真实的故事。因为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,都值得被写进文学里;每一个用心创作的基层作者,都在搭建着连接人心的桥梁。
当飞机降落在中国的土地上,看着窗外熟悉的街道和人群,看着机场里来来往往的人,有的提着行李回家,有的背着书包出发,我知道,这场“采访诺奖故乡”的旅程没有结束,它只是换了一种方式继续。我们会带着在斯德哥尔摩的收获,回到基层作者身边,听老周讲小镇里新发生的故事,听小林说病房里的新变化,听更多人讲他们的生活、他们的热爱。然后把这些故事讲给更多人听,让更多人知道,基层作者的文字里,藏着最真实的生活,藏着最温暖的力量。
因为真正服务基层作者,让每一份真诚的创作都被看见,让每一个平凡的声音都被听见,才是文学最温暖、也最坚定的选择。就像二手书店老人说的那样,好的文字是跨越山海的桥,而我们要做的,就是帮基层作者把这座桥建得更宽、更长,让他们的文字能走到更远的地方,让更多人在文字里,找到自己的影子,找到生活的力量。
喜欢冰阳之歌请大家收藏:()冰阳之歌
请勿开启浏览器阅读模式,否则将导致章节内容缺失及无法阅读下一章。
相邻推荐:我喜欢你,是一辈子的事 我的人生手帐 崩坏曝光:开拓命途冲跨虚数之树 羲和永劫:硫火纪元 修真弟子爱逍遥 苟道修仙:我变成了修真界第一人 那些流浪的日子 轻小说系列:世界最强的无魔力者 全能超神 综影视:炮灰逆袭之路 我在迪迦世界里养怪兽 九天神陨 我是雄虫!不做米虫难道996 蛋黄派 四合院:大领导是我的老政委 我被系统抹杀后她疯了 从外星基地开始崛起 谍锁连环:沉渊 摄政王的逗比特工王妃 排球少年:就做万人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