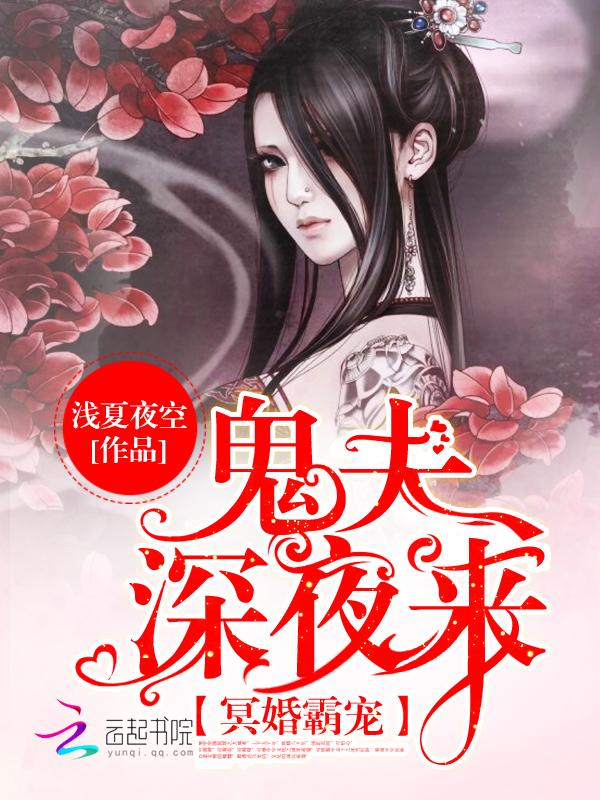630中文网>林冲君 > 浑沦观卷一 本体之论(第2页)
浑沦观卷一 本体之论(第2页)
“他看见:汴梁孩童的哭嚎与巴黎母亲的悲鸣共振;十字军屠城与黄巢起义的血海重叠……所有这一切,皆因我们本就处于一张无边的关系巨网之中,每一个‘点’的震颤,都牵动着整个‘网络’。”(小说原文)
这张“关系巨网”,便是“浑沦”的存在状态。所谓的“分别心”,只是网络中的某个节点(个体)产生的幻觉,误将自己与网络割裂开来。
三、“浑沦”即“身心不二”
“浑沦”观亦超越了灵肉二元论。身体并非心灵的囚笼,心灵亦非身体的幽灵。身心一如,皆是“气”的不同存在样态。心是气之灵明知觉的功能,身是气之凝聚有形的状态。王夫之在阐释张载思想时深刻指出:“形也,神也,物也,三相遇而知觉乃发。”(《张子正蒙注·太和篇》)知觉的产生,是形体、精神与外物三者相遇感通的结果,三者统一于气化的过程之中。
林冲的觉悟历程,正是从“以武卫道”(偏重身体技艺)到“以和护生”(调和身心内外),最终达到“情证道”、“无无大成”(身心彻底融通,情感化为最高能量)的“浑沦”之境。
结论:浑沦非理想,乃实相
因此,“浑沦”绝非一个需要我们去努力达成的理想乌托邦。恰恰相反,它是我们无法逃脱的存在论事实。我们从未离开过“浑沦”,正如鱼从未离开过水。我们只是时常用概念的刀锋、欲望的壁垒,为自己营造了一种“独立自存”的幻觉,从而“遗忘”了这本然的浑沦状态。
《蹈刃者》的寓言之所以深刻,在于它揭示:最大的灾难(魔劫)并非外来袭击,而是源于对这种“浑沦”实相的集体性遗忘与背叛(构建剥削链);而最终的救赎,也非依靠外力拯救,而是依靠对这本然实相的集体性重新觉醒(烙印共生之印)。
“浑沦”,于是从一个古老的词汇,跃升为我们这个时代最亟需的哲学视角。它要求我们摒弃根深蒂固的分别心,重新学会用一种参与式的、关系性的、整体性的眼光,来审视自我、看待世界、理解存在。它告诉我们,世界的真相,从来就不是一堆彼此分离的原子,而是一张永恒振动、交织共鸣的浑沦之网。我们,皆是网中经纬,呼吸与共,痛痒相关。此乃世界的实相,而非理想。认清此实相,方是构建任何真正伦理与美好生活的起点。
第二章“共生之印”的哲学阐释
第一节“印”在内不在外:共生的本体论事实
“共生之印”,绝非额间一点朱砂,亦非神明外力强加的道德枷锁。若作此解,便是再度堕入了主客二分的窠臼,将其视为一个可以剥离、可以赠予的“外在标记”。本书所要阐明的核心要义在于:“共生之印”首先且根本的,是一个内在于每一个体、先于一切自觉意识的本体论事实(ontologicalfact)。它不因你是否承认、是否感知而改变,它就是我们存在的基本方式与构成条件——我们先天就被抛入、并且始终置身于一个与万物、与他人相互依存、相互构成的共生关系网络之中。
此一论断,并非诗意的想象,而是有着坚实的气论哲学基础。张载的“气本论”早已揭示,宇宙万物皆由连续无间的“气”所构成。个体的诞生,并非一个孤立灵魂注入一具孤立肉体,而是天地之气在特定时空条件下的聚结(聚合与凝结)。王夫之阐发道:“气之所至,神必行焉,性必凝焉;故物莫不含神而具性,人得其秀而最灵者尔。”(《张子正蒙注·乾称篇》)意即,气的聚结必然伴随着“神”(意识、精神)的运行与“性”(本性、特质)的凝聚。因此,每一个人,从其生命孕育之初,其“神”与“性”便已先天性地蕴含着与天地万物同源同构的关系性基因。
这个由气之聚散而形成的生命,从其第一口呼吸、第一口哺乳开始,便已无可选择地落入一张巨大的共生关系网络之中。我们的身体,由来自自然界的元素构成,靠汲取外界能量维持;我们的意识,在与他人的互动中形成,由语言、文化所塑造。我们从未作为一个“单子”存在过。正如《蹈刃者》中林冲所最终昭示的:
小主,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,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,后面更精彩!
“所谓‘剥削链’与‘共生链’,并非两条不同的链锁,而是同一张关系巨网的不同面向。众生皆在网中,既是噬人者,亦是被噬者……而‘共生之印’,便是对此浑沦共在关系的深刻觉醒。”(小说原文)
这“关系巨网”,便是我们存在的真实境遇。所谓的“个体”、“自我”,从来都是这张网络的一个纽结(node),是无数关系交汇、作用的暂时性呈现。因此,“共生”不是一种需要我们后天去努力达成的道德理想,而是我们无法逃脱的存在论命运。区别仅在于,我们是如同梦游般无意识地、甚至以撕裂此网络的方式(如剥削)存在,还是能够清醒地、负责任地(仁爱)去存在。
因此,“印”非外力所烙,而是内蕴于我们存在本身的结构之中。它就是我们作为“关系性存在”的本体论规定性。认识到这一点,是一切伦理思考的绝对起点。它意味着,任何试图追求绝对独立、自足、乃至凌驾于网络之上的“自我”,都是一种存在的幻象,最终只会导致自身的异化与网络的破损,从而引发系统性的危机(魔劫)。而真正的觉醒与自由,始于欣然承认并勇敢承担这一与生俱来的“共生之印”,在于意识到:
吾之存在,即是为共生作证。
第二节“仁”之新诠:从“爱人”到“觉联”
若第一节确立了“共生之印”作为内在于人的本体论事实,那么紧随其后的便是:人应如何面对这一事实?儒家的回答核心而千古不移——曰“仁”。然而,在“浑沦观”的视野下,我们对“仁”的理解必须超越惯常的道德训诫层面,深入其存在论根基,予以重新阐释:“仁”,即是主体对内在“共生之印”的自觉(awareness)、承认(recognition)与承担(responsibility)。传统的“仁者爱人”,其本质并非一种居高临下的情感施予,而是“仁者觉联”——即觉醒于万物之间的普遍联系(Connectedness),并为此种联系的健全与美好负起责任。
此一阐释,与晚清思想家谭嗣同在其旷世之作《仁学》中的理念深度契合。谭嗣同以“以太”释“仁”,提出“仁以通为第一义”的革命性观点。他认为,世间种种阻碍与苦难,皆源于“不通”——塞塞、隔阂、分别。而“仁”的力量,正在于破除这些隔阂,实现“中外通”、“上下通”、“人我通”、“男女内外通”,乃至“虚实通,通之义也,万事万物,莫不有通之理”。此“通”,并非物理上的连接,而是指生命、能量、意识之间的流通无碍、相互感通的状态。这无疑是对儒家“万物一体”观的极大深化与近代化转译,与《蹈刃者》中“能量网络”的设定及“剥削链”所揭示的“不通”之恶,形成了惊人的互文。
在“浑沦”的本体论基础上,“通”即是“仁”在世间的显现方式与实现路径。一个“仁者”,便是一个最大限度地保持并促进自身与外界“通”的状态的人。他她不是封闭的堡垒,而是开放的枢纽。他她能“感”——能对他者的痛苦与喜悦产生真切的共情(empathy),因为深知彼此在本体上的相连(“气”之相感)。他她能“应”——能做出恰当而负有责任的回应(response),因为明了自身的每一个行动都将在关系网络中激起涟漪。
因此,“仁者爱人”的本质,绝非一种孤立的、主观的“情感偏好”,而是源于并印证了这种“觉联”的深度。它意味着:
1.觉知(Awareness):清醒地意识到自我并非孤岛,而是无边网络中的一个节点,与所有其他节点(他人、万物)休戚相关。这正如林冲在化身晶体后,所昭示给世人的那个无可辩驳的真相。
2.联结(Connection):主动打破小我的私欲壁垒,让生命处于一种向世界开放的“通”的状态,体验并承认这种一体性。
3.责任(Responsibility):由这种“觉”与“联”自然生发出关怀与为之负责的冲动。因为伤害他人、破坏自然,在存在论上无异于自戕;而促进他人的福祉、维护生态的和谐,即是巩固自身存在的根基。
于是,“仁”便从一种个人的、或许偶发的道德品质,升华为一种宇宙性的存在论原则——即维系与促进“浑沦整体”之生机与和谐的根本法则。个体的“仁”,便是对此宇宙法则的自觉遵循与践行。
小说中,林冲最终的牺牲,正是这种“仁”的最高体现。他并非以力碾压,而是以自身的存在(化身晶体)去促成全体成员的“觉联”。他让每一个人“看见”了那条将自己与他人紧密相连的“链”,从而由内而外地唤醒那份本应内在于每一个体的、对“共生之印”的承认与责任。
故而,“仁者”并非道德的完人,而是存在的醒者。他她深刻地体会到:“我”的边界是流动的,“我”的存在是交织的。“爱人”,便是在这份深刻的觉醒中,最自然、最必然的行动流露。它不再是“我”对“你”的施舍,而是“大我”对自身网络的维护与滋养。此即“仁者觉联”的真义,亦是应对现代性孤立与割裂的一剂古老而崭新的哲学良方。
这章没有结束,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!
第三节人之新义:五伦枢纽与天地之心
倘若“共生之印”是存在的底色,“仁”是对此底色的自觉,那么,基于此,我们必须对“人”自身进行重新的审视与定义。在浑沦观的视野下,人绝非西方启蒙传统所设定的那种孤立的、原子式的、先于社会关系的理性个体。人,从其本质而言,是一种关系性的存在,其真实性恰在于其身处关系网络的核心,并能动地维系与塑造着这些关系。具体而言,人乃是“五伦”网络的枢纽。
传统的“五伦”(父子、君臣、夫妇、长幼、朋友)并非一套外在的社会规范或道德枷锁。相反,它是儒家对人之存在最根本、最自然的关系境遇的深刻描述。每一个人,自出生起便无可选择地落入父子、兄弟之伦中,其后逐步步入夫妇、朋友、君臣(可现代性理解为社会公民关系)之伦。这五对关系,构成了一个人无法逃脱、并藉以成就自我的基本关系架构。人,正是在处理、平衡、滋养这些伦常关系的过程中,锤炼品德、实现价值、获得存在的意义。人不是一个孤点,而是所有这些关系线的交汇点,是一个动态的“枢纽”。
然而,人绝非关系的被动产物。其伟大与尊严,正在于他能动地处于“三才”(天、地、人)之中,所拥有的那份独特的独立性与包容性。
独立性,体现在“人者,天地之心也”(《礼记·礼运》)。此“心”,非指一器官,而是指知觉、灵明与能动性的核心。天地虽生生不息(天地之德),却“无心”于审视自身、赞美自身、有意识地完善自身。而人,独得天地之秀气,拥有反思、理解并主动参与天地化育进程的能力。天地间的生生之德,需要透过人的自觉意识与实践,才能得到最充分的彰显与实现。这便是人的主体性与独立性——不是脱离天地的独立,而是能自觉担当、主动效法天地的独立。
包容性,则体现在此“心”乃是“天地人同心之心”。人的心,并非一个封闭的内在世界。它所能感通的范围,理论上可及于天地万物。张载言“大其心则能体天下之物”,王阳明言“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”。人心之伟大,正在于其能突破形骸之私,将天地万物涵纳于自身的关切与责任之中,达到与天地万物同呼吸、共命运的境界。这份心灵的无限包容性,是人之尊严的至高体现。
由此,人的尊严便有了双重内涵:一在于其能动地作为“关系枢纽”的实践尊严(在五伦中尽份尽责);二在于其灵明地作为“天地之心”的超越尊严(体察并参与宇宙之化育)。
最后,这一切的动能何在?在于情感。儒家绝非冰冷的理性主义,它始终认为,推动人去践行“仁”、去维系“关系”的根本动力,是真实而炽热的情感。对家国的忠,对伴侣的贞,对父母的爱,对朋友的信,乃至对天地万物的爱惜与欣赏,皆是此种情感动力的流露。此情感并非盲目的冲动,而是经文明熏陶、理性调适后,最为醇厚而强大的力量。它是“浑沦”本体在人心中的脉动。
因此,忠贞是情感动力在伦理中的极致体现,而美,则是情感动力在艺术中的自由表达。它们同源而异流,共同证明了人是一种能以情相感、以爱相连、以美升华的存在。正是这份内在的情感动力,驱动着人去主动地认识那“共生之印”,去自觉地践行那“仁者觉联”,最终在关系的网络中,既成就一个独特的自我,也回应那“天地之心”的崇高召唤,在宇宙的浑沦之境中,找到人之为人的伟大坐标。
第三章浑沦之“用”:中庸的再发现
第一节中庸绝非折中:动态系统的极致平衡
“中庸”二字,世人所误解久矣!常将其等同于“折中主义”,视为无原则的调和;或贬斥为“妥协之道”,以为是向现实压力的无奈屈服。此等见解,实乃买椟还珠,完全错失了儒家这一核心思想的深邃与雄健。在浑沦观的视野下,中庸绝非在两端之间取一个机械、僵死的中间点,而是在一个复杂、动态的关系网络中,为求其整体和谐与生生不息,而进行的一种极致精微的系统调节艺术。它追求的不是静态的“中点”,而是动态的“中道”;不是无原则的“和稀泥”,而是有方向的“致中和”。
《中庸》原文开篇即言:“中也者,天下之大本也;和也者,天下之达道也。致中和,天地位焉,万物育焉。”此言已极分明。“中”,是天下万事万物运行的根本依据(大本);“和”,是通达于天下的普遍规律(达道)。而“致中和”,则是让天地万物各安其位、各遂其生的崇高目标与能动过程。此一过程,岂是简单的“对半开”或“各打五十大板”所能概括?它要求主体深刻洞察系统全局,在万千种力的拉扯中,找到那个能让整体系统最具生机、最为和谐的最优平衡点。
此“最优平衡点”绝非固定不变。它随时间、情境、因缘的变化而流动不居。因此,践行中庸之道,需要如高手操舟,时刻感知水流、风向、舟身之微毫变化,并作出精准而及时的调整。这正契合孔子所言:“君子之中庸也,君子而时中。”(《中庸》)所谓“时中”,便是随时而中,在每一个当下都能做出最恰如其分的回应。这是一种至高难度的实践智慧,要求主体既要有对“浑沦整体”的深刻洞察(明体),又要有在具体情境中灵活应变的卓越能力(达用)。
这章没有结束,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!
请勿开启浏览器阅读模式,否则将导致章节内容缺失及无法阅读下一章。
相邻推荐:温水锅里有个炸弹 迷心妄想 言行合一 西年 校花们的露出日记 诱他 在银月大陆被系统精灵害成绿帽龟奴 你的声音 与堂妹换亲后,糙汉夫君宠她成瘾 重生:从妈妈开始 为了避免受伤我无限升级 霓虹灯影 抛开道德的束缚 炼妖成仙:这个家族全是老六 禁区之外:开局解锁文明火种 玄元太子修道录 穿越者宇智波补完计划 【修仙gl】天道第一情 我在网游里点满奇葩技能 逆爱沉沦:蛇夫他日夜索糖
![(综同人)[综]别怕,我是鬼+番外](/img/451325.jpg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