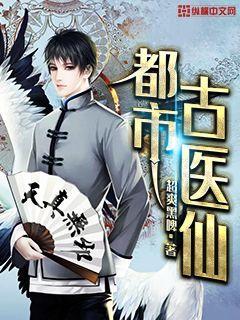630中文网>大明养生小帝姬 > 第41章 东光纪事烟火人间(第2页)
第41章 东光纪事烟火人间(第2页)
本小章还未完,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!
沈砚接过词集,郑重地作揖:“多谢老先生,晚辈定当好好保管,教孩子们记着致远公的心意。”
往驿馆走的路上,夕阳把众人的影子拉得长长的。朱由校躺在李嬷嬷怀里,手里攥着那本《东篱乐府》,已经睡着了,小脸上还带着笑;朱徵妲靠在张嬷嬷肩头,捏着风车的小手渐渐松了,也睡着了。
“沈先生,你看那卫河上的船。”张清芷指着远处的卫河——夕阳下,几艘漕船正扬帆起航,船头的“漕”字旗在风中招展,船工们的号子声顺着风飘过来,不再像往日那般沉重,倒透着股轻快劲儿。
沈砚望着远处那片金色的芦苇荡,又看了看怀里抱着书睡着的朱由校,轻声说:“这东光的秋天,倒比临清更暖些。”李嬷嬷笑着接话:“可不是嘛,孩子们今日笑得比往日都多,可见是喜欢这里。
众人推着小推车,慢慢往驿馆走。卫河的水声、船工的号子声、远处村里的狗叫声,混在一起,像一首温柔的歌。沈砚知道,这东光的半日时光,会和临清的军户、码头的纤夫一样,深深印在两个孩子的心里——或许他们长大后记不清马老先生教写“一”字的模样,记不清染布坊青蓝的布幡,却一定记得卫河边暖融融的夕阳,记得风车转起来时“呼呼”的响,记得有人在他们耳边说“百姓安稳,才是真的好”。
回到驿馆时,天已擦黑。店小二早把晚饭备在大堂的小桌上——两碟素菜,一碟炒南瓜,一碟凉拌芦苇芽,还有一盆粟米粥,旁边摆着四个白面馒头,是特意给孩子们蒸的。李嬷嬷先抱着朱由校去里屋擦洗,张嬷嬷抱着朱徵妲跟进屋,沈砚则和张清芷、周文、刘三坐在桌边,说起明日往德州去的行程。
“方才去码头问了,明日辰时会有艘往德州的漕船,是赵大人派来接咱们的,船工都是临清认识的老漕夫,稳妥。”周文边说边给沈砚盛了碗粥,“戈子谦那边也打听了,下午已把贪墨的银子全拿出来,修船厂的李老三正带着人补漕船,衙役也把管家押去了县衙,只等咱们明日走后,县衙再上报德州府处置。”
沈砚点点头,刚要端起粥碗,就听见里屋传来朱徵妲的哭声——原是张嬷嬷给她解小袄的抽绳时,不小心拽到了她的小胳膊。沈砚连忙起身往里屋走,见朱徵妲趴在张嬷嬷怀里,小脸皱成一团,眼泪“吧嗒吧嗒”往嬷嬷衣襟上掉,小胳膊还一抽一抽的。
“怎么了?”沈砚轻声问。张嬷嬷慌得手都抖了,忙把朱徵妲的小胳膊抬起来看:“方才解绳时没注意,许是拽着了,没肿也没红,就是吓着了。”沈砚走过去,轻轻握住朱徵妲的小胳膊,慢慢揉着她的胳膊肘,又掏出块糖——是早上马小乙送的那块糖人剩下的糖渣,用帕子包着,还没化透。他把糖递到朱徵妲嘴边,柔声哄:“郡主乖,吃糖就不疼了,你看哥哥还在笑你呢。”
果然,里屋床沿上,朱由校刚擦洗完,穿着件小肚兜,正坐在李嬷嬷腿上,手里拿着个白面馒头啃得香,见朱徵妲哭,还伸着小手要去够她的头发,嘴里“咯咯”笑着。朱徵妲见哥哥笑,又闻到糖香,哭声渐渐小了,小口叼住糖块,含在嘴里,小胳膊也不抽了,只委屈地往沈砚身边靠了靠。
我们的小妲妲又开始装嫩了,这才是个不足3岁的孩子样嘛。沈现和张清芷无语的对看一眼。
“还是沈先生有办法。”张嬷嬷松了口气,笑着说。沈砚摸了摸朱徵妲的头,又对李嬷嬷说:“把孩子们的小袄再检查检查,明日坐船风大,抽绳得系紧些,别再刮着了。”李嬷嬷连忙应着,拿起床上叠好的小袄,仔细捏着袖口的抽绳。
第二日天刚亮,卫河上的晨雾还没散,驿馆外就传来了漕夫的吆喝声。李嬷嬷和张嬷嬷早把孩子们收拾妥当——朱由校穿了件青布小袄,外面罩着件薄棉背心;戴着瓜拉帽,朱徵妲穿了件粉色小袄,头上还包了块浅红的头巾,怕雾水打湿头发。俩孩子都被嬷嬷抱在怀里,手里各攥着个热乎的白面馒头,小口小口地啃着。
沈砚一行人出了驿馆,往码头走。晨雾里,漕船的轮廓渐渐清晰——那是艘不大的漕船,船身刷着新漆,船头站着个熟悉的身影,是临清军户营的老漕夫王大叔。见沈砚等人来,王大叔连忙跳上岸,拱手笑道:“沈先生,殿下,郡主,俺们来接你们了!这船是赵大人特意让人检修的,船底的木板全换了新的,稳当得很!”
刘三,周文两人先跳上船,检查了一遍船舱——船舱里铺着厚厚的稻草,稻草上垫着褥子,还摆着两个小靠枕,是给孩子们坐的。张清芷扶着李嬷嬷和张嬷嬷上船,沈砚则抱着朱徵妲,周文抱着朱由校,慢慢往船舱走。戚金等护卫队二十人紧随其后,
刚进船舱,朱徵妲就伸着小手要往船舷去——晨雾渐渐散了,阳光透过雾层洒在卫河上,水面泛着细碎的金光,岸边的芦苇荡像片绿雾,飘在水面上。王大叔站在船头,拿起纤绳,吆喝起了卫河的号子:“哎——起锚咯!卫河水,向东流,载着咱,去德州哟——”
本小章还未完,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!
号子声刚落,船工们就一起发力,漕船缓缓驶离码头。朱由校趴在船舷边,小手指着岸边的芦苇荡,李嬷嬷忙扶住他,怕他摔下去:“殿下慢些,别往前扑。”沈砚也凑到船舷边,指着远处的铁佛寺——晨雾里,铁佛寺的塔尖隐约可见,寺里传来早钟的声音,浑厚悠长,飘在卫河上空,像在给他们送行。
漕船顺着卫河往下游驶,岸边的景色慢慢变了——土坯房渐渐少了,青砖瓦房多了起来,偶尔能看见几座气派的宅院,院门前挂着“耕读传家”的木牌,是东光的书香人家。路过一个叫“李习庄”的村子时,王大叔指着村里的祠堂说:“这村子是永乐年间从山西迁来的,全庄都是姓李的,祠堂里还挂着族谱,写着‘洪武初徙居卫河边,以渔耕为业’——俺娘就是这村里的,小时候俺常来这儿掏鸟窝。”
朱由校趴在船舷边,看着村里的孩子在河边跑,手里拿着芦苇杆追着蜻蜓,也跟着“咯咯”笑起来。张嬷嬷见他高兴,便抱着他往船尾走——船尾的漕夫正摇着橹,橹声“咿呀咿呀”的,和着水流声,格外好听。漕夫见朱由校看过来,笑着从怀里掏出个芦苇编的小蚂蚱,递到他手里:“小殿下,玩这个,俺编的,像不像?”
朱由校接过小蚂蚱,捏着芦苇杆,高兴得直晃身子。朱徵妲见了,也伸着小手要,漕夫连忙又编了个小蜻蜓,递到她手里。俩孩子坐在船舱里,手里拿着芦苇编的小玩意儿,你碰我一下,我碰你一下,笑得格外开心。
沈砚坐在船舱边,看着两个孩子的模样,又望向岸边——李习庄的村口,几个农妇正挎着竹篮往河边走,篮子里装着刚洗好的衣裳,衣裳上还滴着水;一个穿蓝布短褂的青年,肩上扛着锄头,嘴里哼着《汉宫秋》的调子,往地里走,调子虽不成句,却透着股踏实劲儿。他突然想起昨日在致远公故居,马承祖说的话——“致远公叹百姓疾苦,如今能让漕运清明,百姓安稳,便是遂了他的心愿”。
是啊,百姓安稳,才是真的遂了所有人的心愿。临清的军户能好好种地,东光的漕夫能好好行船,李习庄的农妇能好好洗衣,村口的青年能好好种地——这些最寻常的日子,才是这大明朝最结实的根基。
漕船驶离李习庄时,晨雾已全散了。阳光洒在卫河上,把水面照得金灿灿的,岸边的芦苇荡随风摇摆,像在挥手送行。朱由校和朱徵妲趴在船舷边,小手指着远处的村庄,嘴里喊着“再见……再见……”,许是在跟东光的糖人再见,跟染布坊的青布再见,跟致远公故居的石桌再见。
东光的烟火气让两孩子很放松,默契的做了一回三岁孩童该做的事。
沈砚望着渐渐远去的东光城,轻轻翻开怀里的《东篱乐府》——书页上,马致远的词“小桥流水人家”墨迹已淡,却像极了方才看见的李习庄。他知道,这东光的记忆,会和临清的木牌、漕船的号子一起,刻在两个孩子的心里。等他们长大,等他们真的懂了“百姓疾苦”四个字,便会记得,万历三十六年的九月下旬,在卫河边的东光,有暖融融的夕阳,有转起来的风车,有好好过日子的百姓——那是他们身为皇孙、郡主,最该守护的模样。
漕船继续往下游驶,卫河的水声“哗哗”的,像在唱着一首悠长的歌。远处的天空,蓝得像块干净的绸缎,几朵白云飘着,悠闲自在——那是东光最好的一个秋天,也是大明朝漕运史上,最安稳的一段时光。
喜欢大明养生小帝姬请大家收藏:()大明养生小帝姬
请勿开启浏览器阅读模式,否则将导致章节内容缺失及无法阅读下一章。
相邻推荐:前任Ex 开局差评,系统让我当武林盟主 【GB女攻】战神将军与笼中雀(女攻xCountboy) 哥哥好多啊(伪骨NPH) 骚母狗(出轨 偷情 NPH) 不是说建国以后不能成精吗? 三角洲:从跑刀鼠鼠到顶尖护航 万人迷大小姐破产以后(np) 高武:欺我朽木?我以杀戮成神! 禁阙春夜宴(np) 全民领主:凡人三国传 虐恋 (骨科,SM,NPH) 投资我必翻倍,仙子们疯狂争抢 修仙充值一千亿,天才都是我小弟 黑道教父還要生 你要毁了这个家吗(np骨) 四合院之我是贾东旭舅舅 失温(父女H) 高考后我拎古剑,锤爆了幕后黑手 搞事就变强,开局复活长孙皇后