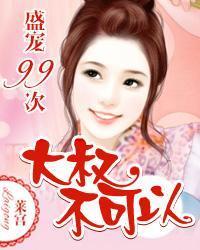630中文网>大明养生小帝姬 > 第67章 诸僚理事破困局(第2页)
第67章 诸僚理事破困局(第2页)
宋明德大喜,又道:“还有件事——义塾的孩子们,好几天没吃热乎的了,你能不能跟‘福记’的李掌柜说声,捐两石杂粮?小米、高粱都行,让老秀才给孩子们熬粥喝。”
“没问题!李掌柜跟我是拜把子兄弟,我现在就去跟他说,让他今天就送粮过去。”王福安说着,就喊伙计,“去,把后屋的三十斤棉絮、十匹粗布包好,傍晚送到西门外义塾;再去‘福记’粮铺,找李掌柜,说宋知州要两石杂粮,捐给义塾,让他赶紧送过去。”
伙计应着跑了,宋明德站起身,作了个揖:“王老板,谢了——你这情,我记着,以后布庄有什么事,尽管找我。”
“宋知州客气了,我这是应该的——孩子们可怜,能帮一把是一把。”王福安笑着说。
小主,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,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,后面更精彩!
宋明德又去了石灰窑——石灰窑在州城北门,窑主姓赵,是个爽快人。宋明德一到窑上,就看见赵窑主在指挥工人装石灰,赶紧迎上去:“赵窑主,忙着呢?”
赵窑主回头,见是宋明德,赶紧停下手里的活:“宋知州,您怎么来了?是不是修堤要石灰?我这刚烧好一窑,有两百斤,您要多少?”
“我要一百五十斤——北关、柳溪修堤,地基要拌石灰夯,不然不结实。可我现在没银钱给你,得欠着,等三月税银收上来,再给你结账,行不行?”宋明德直言道。
赵窑主哈哈大笑:“宋知州,您这说的什么话!修堤是为了保德州的田,我这石灰窑也在德州,堤修好了,我也放心。一百五十斤石灰,我现在就给您装船,送到柳溪堤岸工地,银钱的事,您什么时候有什么时候给,不急!”
宋明德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——棉絮、杂粮、石灰都解决了,修堤、义塾的事都顺了,他哼着小曲,回了州衙,刚进门,就见李二郎带着几个乡勇来报:“大人,钟御史调的二十个流民,我带来了,都在门外等着,什么时候去柳溪修堤?”
“明天一早去——今天让他们先歇着,从伙房领两升粮,让他们吃顿热乎的。”宋明德说着,又道,“明天你跟王家宾去张大户的庄,帮着清田,别让张大户的家丁闹事,要是敢动手,你就把他们绑了,我给你做主。”
李二郎胸脯一挺:“大人放心,有我在,张大户的家丁不敢横!明天保准让王主事顺顺利利和田。”
第二天一早,王家宾就带着两个吏役,在州衙门口等——宋明德派的六个衙役,都穿着皂衣,腰里别着刀,李二郎带着五个乡勇,手里拿着长矛,一行人浩浩荡荡往张大户的庄去。张大户的庄在南坡,离州城有十里地,走到庄外,就见十几个家丁拿着棍子,堵在庄门口,为首的是张大户的管家,叉着腰喊:“干什么的?这是张老爷的庄,不许进!”
王家宾上前一步,手里拿着旧田册:“奉汪巡按令,清核田亩,张大户何在?让他出来接令!”
管家刚要说话,李二郎就往前一站,手里的长矛往地上一戳:“瞎了你的眼!没看见衙役老爷在这?再拦着,就当你们抗官,绑了送州衙!”
管家吓得往后退了一步,里头的张大户听见动静,赶紧跑出来,穿着件绸缎棉袍,脸上堆着笑:“哎呀,是王主事、李队长,误会,都是误会!家丁不懂事,拦着各位,我这就骂他们!”
他一边管家,一边往王家宾手里塞银子:“王主事,一点小意思,您拿着买茶喝,田册的事,咱们好商量,不用这么兴师动众……”
王家宾一把推开他的手:“张大户,别来这套!旧田册上写着你有一百二十亩田,可庄南那片地,我派人量了,就有一百五十亩,你瞒了多少,自己说!今天要是不把实底交出来,就跟我们回州衙,当着汪巡按的面说!”
张大户脸一白,还想狡辩,衙役已经冲进庄里,直奔库房——很快,一个衙役拿着几本新地契跑出来,递给王家宾:“主事,找到了!张大户藏的地契,写着他有两百亩田,瞒了八十亩!”
王家宾把地契往张大户面前一摔:“你还有什么话说?八十亩田,每年欠税银四两八钱,五年就是二十四两,限你正月底前缴清,不缴,就抄你的家!”
“张大户瘫在地上,方才的嚣张气焰荡然无存,脸上肥肉颤抖,仿佛一瞬间被抽走了脊梁骨。他看着衙役手中那几本地契,终于明白,在真正的国家权力面前,他苦心经营的地方势力是如此不堪一击。”他哭丧着脸:“王主事,我缴,我缴!可我现在没那么多银钱,能不能缓到二月?等我卖了家里的粮食,就缴……”
“不行!正月底前必须缴清,少一两都不行!”王家宾斩钉截铁地说,“今天就把田册改过来,按两百亩田登记,要是再敢瞒报,直接押你去临清府衙问罪!”
张大户没辙,只让里正李老四改田册,签字画押——清完田,已经是中午,王家宾带着人往回走,李二郎笑着说:“王主事,您看,早这么来,张大户哪敢不老实?以后清田,您就找我,保准顺利。”
王家宾点头:“还是得靠宋知州的衙役、乡勇,不然光靠我钞关的人,还真治不了他。”
与此同时,钟化民正在李家堡的赈济点——刘老栓已经把藏的五户流民补进册里,张二爷帮着认了人,吏役重新记了账,赈粮券也发下去了。王阿婆拿着粮券,领到了当天的两升小米,激动得直哭:“多谢钟大人,多谢官府,不然我们娘俩,真熬不过这个冬天……”
钟化民又让吏役把两石粮送到刘老栓家,刘老栓抱着粮袋,也红了眼:“钟大人,我错了,以后再也不瞒报了,您放心,以后核册,我跟张二爷一起签字,绝不出错。”
钟化民拍了拍他的肩:“知道错了就好——好好帮着管赈济点,别让流民受委屈,这比什么都强。”
本小章还未完,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!
处理完李家堡的事,他又去了南坡的复耕队——王老实带着八十个流民,正在地里松地,虽然犁铧不够,但铁匠铺送来的十把修好的犁铧,正好用上,流民们两人一组,一个扶犁,一个拉犁,干得热火朝天。见钟化民来,王老实跑过来:“大人,您放心,再有十天,南坡的五十亩田就能耕完,赶得上种麦。”
“犁铧够不够?不够就跟我说,我再去催铁匠铺。”钟化民问。
“够了够了——铁匠铺说明天再送十把来,有二十把犁铧,够我们用了。”王老实笑着说。
徐光启那边,给彰德府的信已经送出去了——他怕驿卒走得慢,特意找了个快马,加了二两银子,让驿卒务必在正月廿前送到。写完信,他又去了西仓——泥瓦匠正在换瓦,这次没敢耍滑,新瓦铺得整整齐齐,徐光启拿着尺子,量了量瓦的厚度,又查了地基,满意地点头:“二月初能完工吧?”
瓦匠头赶紧点头:“能!您放心,我们加把劲,正月廿八就能完工,赶在种粮运回来之前,保准没问题。”
徐光启又去了西仓的陈粮堆——五个吏役正在晒粮,把没霉透的陈粮摊在席子上,翻来覆去晒,徐光启抓了把粮,看了看:“晒干净点,挑出霉粒,别让农户种下去出问题。这五十石粮,能种一千亩田,也是救急。”
吏役应着:“大人放心,我们天天在这晒,保准挑干净。”
到了正月廿,彰德府的回帖终于来了——这次的回帖,语气比上次热络多了,周文彬在信里写:“番薯种一事,甚合本府之意,特匀出麦种五十石、棉种二十石,合计四百石麦种、七十石棉种,脚银仍按原议三十两,派船至彰德府码头即可,无需加钱。另,本府农师李修远,愿随船赴德州,学习番薯试种技术,望徐布政妥为安排。”
徐光启拿着信,一路跑到总办房,喊着:“汪巡按,成了!彰德府同意多借五十石麦种、二十石棉种,脚银不加了,还派农师来学番薯种!”
汪应蛟正在看王家宾的清田报帖——张大户已经缴了十五两税银,剩下的九两,说正月廿八前缴清,北关、柳溪的清田也完了,没再发现瞒田的事。见徐光启高兴,他也笑了:“好!周文彬果然是懂农政的,这下种粮够了。你赶紧安排船,正月廿五去彰德府运种粮,让李农师跟着回来,就在东皋设试种田,好好教农户种番薯。”
徐光启点头:“我这就去安排——船已经找好了,是德州卫的漕船,船工都是老手,不怕运河冰没化透。”
正月廿五,漕船从德州出发,去彰德府运种粮;正月廿六,宋明德派人来报,柳溪的堤岸换土完工,开始填石灰夯土,北关的堤岸也修了八十丈,三月底前能完工;正月廿七,钟化民来报,复耕队耕完了南坡的五十亩田,开始去东皋耕田,犁铧够了,流民干劲足;正月廿八,汪应蛟带着书吏,去各乡堡巡查——李家堡的赈济点,流民领着粮,喝着防瘟汤药;东皋的试种田,徐光启正带着农师李修远,看番薯种的晾晒;柳溪的堤岸,乡勇、流民正在夯土,号子声震天;义塾的孩子们,穿着新缝的粗布棉衣,喝着小米粥,在院里读书。
张大户也缴清了剩下的九两税银,低着头跟汪应蛟保证:“以后再也不敢瞒田了,好好缴税,绝不给官府添麻烦。”
汪应蛟看着眼前的景象,心里踏实了——正月的麻烦,一件一件破了,赈济点稳了,种粮够了,堤岸在修,复耕在赶,税赋的窟窿也堵了。虽然还有些小事没办完——吏役的俸禄只补了一个月,番薯种还没试种,堤岸还得赶工期,但只要照着规划办,一步一步来,德州的春耕,肯定能成。
“回到州衙,已是傍晚。夕阳的余晖穿过寒冷的空气,温暖地照在州衙的青瓦上,也照在总办房那堆积如山的报帖上。那不仅是待办的公务,更是他们用一整个正月的心力,为这片土地破开困局、点燃的星星之火。”
喜欢大明养生小帝姬请大家收藏:()大明养生小帝姬
请勿开启浏览器阅读模式,否则将导致章节内容缺失及无法阅读下一章。
相邻推荐:前任Ex 高考后我拎古剑,锤爆了幕后黑手 三角洲:从跑刀鼠鼠到顶尖护航 骚母狗(出轨 偷情 NPH) 失温(父女H) 四合院之我是贾东旭舅舅 搞事就变强,开局复活长孙皇后 哥哥好多啊(伪骨NPH) 不是说建国以后不能成精吗? 万人迷大小姐破产以后(np) 投资我必翻倍,仙子们疯狂争抢 【GB女攻】战神将军与笼中雀(女攻xCountboy) 禁阙春夜宴(np) 你要毁了这个家吗(np骨) 修仙充值一千亿,天才都是我小弟 黑道教父還要生 虐恋 (骨科,SM,NPH) 高武:欺我朽木?我以杀戮成神! 全民领主:凡人三国传 开局差评,系统让我当武林盟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