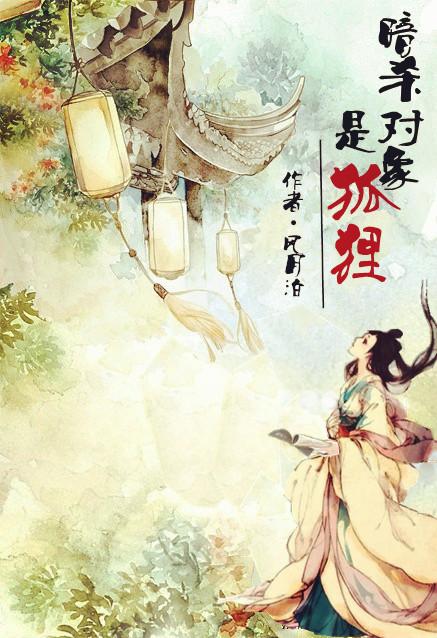630中文网>大明养生小帝姬 > 第67章 诸僚理事破困局(第1页)
第67章 诸僚理事破困局(第1页)
正月官衙忙实务诸僚理事破困局
德州州衙的总办房里,自打正月初十过了,就没断过人——案头堆着刚送来的《赈济点核册报》《仓房修缮进度》《钞关卡子日志》,还有宋明德派人送来的《堤岸施工簿》,每张纸都写得密密麻麻,边角沾着泥点、炭灰,一看就是从乡堡、工地直接递上来的。汪应蛟一早就在房里坐着,手里捏着支狼毫,逐页划着重点,时不时停下来喊书吏:“把钟御史的报帖取来,跟宋知州的施工簿对对——以工换赈的流民数,怎么跟修堤的人数对不上?”
书吏刚把报帖找出来,门外就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,钟化民掀着棉帘进来,脸冻得通红,棉袍下摆沾着雪水,一进门就直奔案头:“汪巡按,李家堡的赈济点出了点岔子——核流民册的时候,里正刘老栓藏了五户流民,说是‘怕官府嫌人多,断了赈粮’,我让他把人交出来,他倒好,抱着柱子哭,说交出来就活不成了,您说这事儿……”
汪应蛟放下笔,指了指旁边的椅子:“坐,喝口热茶慢慢说——流民册怎么核出来的?乡老没帮着认人?”
钟化民端过茶盏,猛灌了一口,才缓过劲:“您忘了,上个月定的规矩,核册要乡老认人、吏役记账。李家堡的乡老是张二爷,七十多了,眼不花,记性好。今早我让吏役念流民名字,张二爷听着听着就摇头,说‘王阿婆、李狗子这五户,明明在村西头草棚住着,怎么没在册上?’我就问刘老栓,他一开始说‘那五户是外乡来的,刚走了’,张二爷当场就戳穿了——说昨天还见王阿婆去河边淘米,哪能走?刘老栓没辙,才说怕人多了,咱们的赈粮不够,藏着不报,想自己凑粮养着,可他那点家底,哪养得起?”
“我去村西头看了,那五户流民挤在两间破草棚里,铺的是稻草,盖的是破棉絮,有个小孩冻得直哭,手里攥着半块冻硬的窝头。刘老栓也真可怜,家里就两亩薄田,涝后没收成,还掏了自己的口粮给流民,可他不该瞒报——一瞒报,流民领不着赈粮券,真冻饿出事儿,谁担责?”
汪应蛟皱着眉,手指在案上敲了敲:“刘老栓不是坏心,是糊涂——他以为藏着人能保平安,其实是把人往死路上推。这样,你回去跟他说:第一,藏的五户流民,立刻补进册里,发赈粮券,一天一领,少不了他们的;第二,他掏的口粮,从赈济点的余粮里补给他——按五户人十天算,补两石粮,不能让实心办事的人吃亏;第三,让张二爷盯着他,以后核册,里正得跟乡老一起签字画押,再瞒报,就不是哭一哭能过去的了。
钟化民点头:“我也是这么想的,就怕他不信官府能补粮,所以来跟您吱一声,有您这句话,他就踏实了。对了,以工换赈的队,我昨天编好了——西门外的流民一百二十人,欠饷的乡勇八十人,合起来两百人,分两队:一队一百人去修堤,归李二郎管;一队一百人去帮农户复耕,归东皋的里正王老实管。复耕的队昨天已经去了南坡——南坡有五十户农户的田没耕,冻土层刚化,正好趁墒情松地,农户给一升粮,官府补一升粮,流民干劲足着呢,就是……”
他顿了顿,又道:“就是复耕的农具不够——农户自己的犁铧,有一半是坏的,涝后没来得及修。我让吏役去州城的铁匠铺问,铁匠说要修犁铧,得要铁料,可铁匠铺的铁料年前就用完了,得等临清的铁商来,最快也得正月底。没犁铧,光靠锄头挖,一天耕不了半亩地,这春耕赶不上啊。”
汪应蛟刚要开口,门外又有人来——这次是徐光启,手里拿着封文书,脸色比钟化民还沉:“汪巡按,彰德府的回帖来了——说今年河南也缺种粮,四百石麦种、八十石棉种,只能借三百石麦种、五十石棉种,还得咱们自己派船去运,脚银得加三成,说是‘运河冰没化透,船工要加钱’。这哪是借种,简直是敲竹杠!”
他把文书往案上一放,指着上面的字:“您看,彰德府粮储道写的——‘本府春播亦需种粮,勉力匀出三百五十石,船工脚价纹银四十五两,限正月廿五前运走,逾期不候’。咱们原计划脚银三十两,现在多要十五两,种粮还少了一百三十石,这春耕的种粮不够啊!东皋、南坡那八千亩田,按每亩五升麦种算,就得四百石,现在只借到三百石,差一百石,棉种也差三十石,这可怎么办?”
钟化民也凑过来看,眉头皱得更紧:“差一百石麦种,够两千亩田没种的——总不能让农户空着地吧?要不,从德州的陈粮里筛筛?西仓不是还有二百石陈粮吗?挑些没霉透的,晒干净了当种粮?”
徐光启立刻摇头:“不行!陈粮霉了一半,就算晒干净,出芽率也低,农户种下去,苗长不好,秋后没收成,得闹乱子。我昨天去西仓看了,那二百石陈粮,只有五十石还能凑活,剩下的都得拉去沤肥,根本当不了种粮。”
小主,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,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,后面更精彩!
“汪应蛟拿起文书,翻来覆去看了两遍,心中瞬间闪过几个念头:硬顶回去,春耕危矣;全盘接受,官威扫地,且财政吃紧。忽然,他想起三年前京城旧事……随即问徐光启:‘彰德府的粮储道姓什么?叫周文彬?’”我记得三年前在京城见过他,他是个懂农政的,不是会敲竹杠的人——是不是有别的难处?你给彰德府的信里,提没提咱们要推番薯种的事?”
徐光启一愣:“没提——我只说借麦种、棉种,没说番薯种。您提这个干什么?”
“你再写封信,就说德州从福建调了两百斤番薯种,正月底能到,想请彰德府农师来看看番薯试种——周文彬当年在京城就问过番薯种的事,说河南旱田多,想试试种番薯。你就说,要是他能多匀五十石麦种、二十石棉种,咱们的番薯种收了之后,分他一半当谢礼,再请他的农师来德州学试种技术。”汪应蛟手指点着文书,“他不是缺种粮,是怕咱们借了不还,又没好处——番薯种是新鲜东西,他肯定想要,你试试这个法子,说不定能成。”
徐光启眼睛一亮:“对啊!我怎么没想到这个?周文彬懂农政,肯定看重番薯种。我这就去写,让驿卒快马送过去,赶在正月廿前送到彰德府,还能来得及。”
他刚要走,汪应蛟又喊住他:“仓房修缮怎么样了?正月初十动工,今天都正月十七了,西仓那四间房,修得怎么样了?别到时候种粮运来了,仓房还没修好,堆在院里冻着。”
“我昨天刚去查过,泥瓦匠耍滑——原计划换新瓦,他们把旧瓦翻过来再用,说‘旧瓦还能用,省点材料钱’,我当场就把瓦匠头骂了一顿,让他把旧瓦全换下来,用新瓦。现在重新换瓦,得耽误三天,二月初才能完工,赶在正月廿五运种粮回来,还能凑活。”徐光启说着,又补充道,“材料钱超了十两——新瓦比原计划贵,我从库房里的七百六十两里挪了十两,现在库房还剩七百两,吏役的俸禄只够补一个月的,剩下的欠饷,还得靠王家宾那边的税银。”
汪应蛟点头:“仓房必须修好,材料钱超了就超了,别省这点钱,以后漏雨更麻烦。你先去写借种的信,瓦匠那边盯着点,别再出岔子。”
徐光启刚走,王家宾就来了,这次倒是一脸笑意,手里拿着本账册:“汪巡按,钞关的卡子立住了!沙沟河那三个卡子,从正月初十到十七,一共拦了十二艘逃税的商船,追缴税银八十七两,还抓了个惯逃的船主——叫赵老三,每年都绕着钞关走,这次被下游卡子的巡卒抓了,缴了他二十两税银,还罚了十两,让他给其他船主当例子。现在商船都不敢绕路了,要么走主运河过钞关,要么走沙沟河登记拿路引,税银收得比上个月多了两成。”
他把账册递过去,翻到其中一页:“您看,这是这七天的税银——主运河收了三百二十两,沙沟河收了八十七两,合计四百零七两,比去年同期多了八十七两。巡卒的饷银加了二两,他们也上心,夜里顶着雪巡逻,没一个偷懒的。对了,临清钞关那边也通了气——他们登记的商船,要是没到德州缴税,就知会咱们的卡子拦着,现在逃税的少多了。”
汪应蛟看着账册,脸色稍缓:“好,这窟窿堵得不错——沙沟河的卡子,再加两个巡卒,夜里冷,轮班勤点,别让巡卒冻着。清田册的事怎么样了?张大户那边,去核田了吗?”
王家宾的笑意立刻淡了:“别提了,张大户那边刚出了岔子——正月十五我让人去清田,带着旧田册,跟里正李老四一起去的。到了张大户的庄外,他雇了十几个家丁,拿着棍子拦着,说‘我的田我自己清楚,不用官府核’,还说‘李老四是里正,他都没说我瞒田,你们钞关的人管得着吗?’李老四在旁边不敢说话,我派去的吏役跟家丁吵起来,差点动手,最后只能先回来了。”
“我猜,李老四肯定收了张大户的好处——旧田册上写着张大户有一百二十亩田,可我派人去庄外量,光庄南的那片地就有一百五十亩,肯定瞒了八十亩。现在家丁拦着,进不了庄,核不了田,怎么办?我想请宋知州派几个衙役跟着,再去一次——衙役带了刀,张大户不敢拦,不然这清田册的事,就卡在他这了。”
汪应蛟刚要说话,门外传来宋明德的大嗓门:“谁要找我派衙役?我正好来了!”
众人回头,只见宋明德披着件旧棉甲,手里拿着个施工簿,脸上沾着泥,一进门就喊:“汪巡按,修堤的事,有好有坏——好消息是,北关的堤岸,冻土化透了,已经填了五十丈,夯得实实的;坏消息是,柳溪的堤岸,地基软,挖下去三尺全是泥,得换土,不然修了也得塌。换土得要人力,我把复耕队的二十个流民调过来了,可还是不够,还得再要二十人——钟御史,你那边的复耕队,能不能再调二十人?”
钟化民立刻道:“能调——复耕队昨天耕完了南坡的十亩田,剩下的四十亩,缓两天没事,我让王老实带二十人去你那,明天一早就到。”
本小章还未完,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!
宋明德点头,又看向王家宾:“你要衙役是吧?张大户那厮,我早听说了——去年涝后,他还吞了里正给的赈粮,我早想治他了。你明天去清田,我派六个衙役跟着,都带刀,再让李二郎跟去——李二郎是乡勇队长,能打,张大户的家丁再横,也不敢跟衙役、乡勇叫板。你放心,明天保准让你进庄核田。”
王家宾松了口气:“有宋知州这话,我就放心了——明天一早,我在州衙门口等衙役,咱们一起去张大户的庄。”
汪应蛟见几个人的事都有了着落,才开口:“现在几件事定了:钟御史,一是解决李家堡的流民册,补粮给刘老栓;二是调二十个复耕流民去修堤;三是跟铁匠铺说,让他们先修最急用的犁铧,铁料到了再补,实在不行,从州衙的兵器库里找些废铁,熔了修犁铧——总不能耽误复耕。”
“徐布政,一是写封信给彰德府的周文彬,提番薯种的事,多借五十石麦种、二十石棉种;二是盯着西仓的仓房修缮,别再让泥瓦匠耍滑,二月初必须完工;三是把西仓的五十石陈粮晒干净,预备着补种粮的缺口,能种一亩是一亩。”
“王主事,明天跟宋知州的衙役去清张大户的田,核清楚了,欠的二十四两税银,限他正月底前缴清,不缴就押到州衙;清完张大户,再去北关、柳溪的里正那核田,别再出瞒田的事;钞关的卡子,加两个巡卒,夜里轮班,别让逃税的商船钻空子。”
“宋知州,一是调二十个复耕流民去柳溪换土修堤,盯着施工,三月底前必须修完;二是派衙役帮王家宾清田,治治张大户的嚣张气焰;三是去州城的石灰窑问问,修堤要的石灰够不够,不够就先欠着,开春用税银还,别让修堤缺材料。”
他顿了顿,又道:“正月廿五,彰德府的种粮要运回来,徐布政你安排船,王家宾从钞关税里先垫四十两脚银,多出来的十五两,也从钞关税里出——先把种粮运回来再说。正月廿八,我去各乡堡巡查,看赈济点、修堤、复耕的事,都办得怎么样了,谁要是没办好,别跟我找借口。”
几个人都应下来,刚要走,书吏又跑进来,手里拿着张帖子:“汪巡按,西门外义塾的老秀才派人来报——说义塾的棉絮不够了,三十个孤童冻得没法上课,想请官府补些棉絮,还说孩子们好几天没吃顿热乎的,能不能从赈济点匀点粮过去。”
宋明德一拍大腿:“哎呀,我把这事忘了!上个月说捐钱给义塾,还没来得及去跟商铺说。汪巡按,这事我来办——今天下午我就去州城的‘裕和’布庄、‘福记’粮铺,让他们捐点棉絮、杂粮。布庄的王老板,去年涝后我帮他抢过粮,他肯定愿意捐;粮铺的李掌柜,跟我是同乡,捐两石杂粮没问题。明天一早就把棉絮、粮送到义塾,保准孩子们不冻着、不饿着。”
汪应蛟点头:“义塾的事,就交给你了——孩子们是德州的根,不能冻着饿着。快去办吧,别耽误了。”
几个人这才各自匆匆走了——钟化民要回李家堡处理流民册,徐光启要写借种的信,王家宾要准备明天清田的事,宋明德要去商铺捐棉絮、粮,总办房里又剩下汪应蛟和书吏,案头的文书还堆着,门外的雪又下了起来,可这次没人再愁眉苦脸——麻烦虽多,但一件一件破,总能办得成。
当天下午,宋明德就揣着个布袋子,去了州城的“裕和”布庄。布庄老板王福安正坐在柜台后算账,见宋明德进来,赶紧起身:“宋知州,这么冷的天,您怎么来了?快坐,喝口热茶。”
宋明德也不客气,坐在椅子上,直接说:“王老板,我来是求你帮个忙——西门外的义塾,三十个孤童,都是涝后没了爹娘的,现在棉絮不够,冻得没法上课,你能不能捐些棉絮?不用多,二十斤就够,缝几床被子,孩子们能盖着睡觉。”
王福安愣了愣,随即点头:“嗨,这算什么忙!去年七月涝灾,我布庄的货被淹了,是您派乡勇帮我抢出来的,不然我这布庄早黄了。二十斤棉絮太少,我给三十斤,再给十匹粗布,让孩子们缝件棉衣,别冻着。您放心,今天傍晚我就让伙计送过去,保准耽误不了。”
请勿开启浏览器阅读模式,否则将导致章节内容缺失及无法阅读下一章。
相邻推荐:修仙充值一千亿,天才都是我小弟 你要毁了这个家吗(np骨) 骚母狗(出轨 偷情 NPH) 前任Ex 高考后我拎古剑,锤爆了幕后黑手 万人迷大小姐破产以后(np) 四合院之我是贾东旭舅舅 不是说建国以后不能成精吗? 三角洲:从跑刀鼠鼠到顶尖护航 黑道教父還要生 搞事就变强,开局复活长孙皇后 哥哥好多啊(伪骨NPH) 全民领主:凡人三国传 失温(父女H) 【GB女攻】战神将军与笼中雀(女攻xCountboy) 高武:欺我朽木?我以杀戮成神! 虐恋 (骨科,SM,NPH) 禁阙春夜宴(np) 投资我必翻倍,仙子们疯狂争抢 开局差评,系统让我当武林盟主